蒋文杰是一位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白区南京的《新民报》当编辑,撰写过许多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内幕的文章。被激怒的蒋介石曾亲自下令,以《新民报》“泄露军事机密”“为匪宣传,诋毁政府”的罪名,责令《新民报》永久停刊,蒋文杰等九人也同时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接地下党组织急令指示,蒋文杰用化名避开特务出走南京,经上海飞抵香港,参加刚筹建不久的香港《文汇报》工作,担任国际版编辑。
解放初期,蒋文杰担任过上海《新民晚报》(当时叫《新民报晚刊》,1958年改名为《新民晚报》)的总编辑。1957年,他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当过市委领导的秘书。“文革”期间,蒋文杰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待遇,于1971年被下放到上海市五七干校。我是1973年到五七干校的,就在那里认识了蒋文杰。那年他53岁,我27岁,我称他为老蒋,他叫我小刘。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我们慢慢成了忘年交。
这是一位憨厚的长者。人过中年,体态已微微发福,脸颊上的肉有点松弛,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镜,厚厚的近视镜片一圈一圈像啤酒瓶底,说话有点木讷,嗓门大,略有耳背,对人诚恳、实在。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五七干校”为何物,这是以毛泽东同志1966年5月7日的指示命名的干部学校,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等一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下放了10多万国家机关干部,各省市办的五七干校就更多了。上海市五七干校在奉贤奉城,靠近海边,有500多亩地,供下放干部参加劳动。被精简下放到这里的都是华东局机关和上海市直属机关的干部,他们被统称为“五七战士”,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搞“斗、批、改”。还有受迫害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那里见到过老市长曹荻秋同志和他的夫人石斌同志。
1973年的上海市五七干校已经转型,根据上面“要把五七干校办成新型的党校”的要求,专门从事轮训现职在岗干部。我是参加理论班学习结束后被留在了五七干校教研组的。五七干校规定每月只能休假回市区一次,所以我们这些“五七战士”几乎朝夕相处。
我常常跑到老蒋住的平房小屋里,五七干校的房屋都很简陋,上厕所和洗漱用水都要跑到屋外。老蒋喜欢读书,除下地劳动外,他几乎总在伏案看书,习惯性地把眼镜摘放在一边,整个脸贴着书桌,鼻尖几乎要碰触到书,眼睛瞪得老大,随着一行行小字不时左右移动,偶尔拿起笔在本子上抄录着什么。书桌上经常同时摊着几本书,也有大学的校刊,似乎在研究着什么。在我以后与他交往的40多年中,无论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他这种伏案的形象几乎一成不变。
如今我已过了古稀之年,老蒋则已在2015年3月仙逝,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他生前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机关的悼词高度评价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
老蒋知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们都对他很尊重。但他在五七干校似乎没有地位,每当开会时,他总是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墙角边,从不发言。他不像我们可以到轮训班去给学员讲课,与学员一起参加讨论、交流。他的工作是不露面的,为教研组收集一些教学资料,提供教学服务。有人告诉我,老蒋因新中国成立前风风雨雨的许多复杂经历吃了不少苦头,他的脾气很倔,不愿见风使舵,曾经寻过短见:有一天,他突然在五七干校失踪了。当地农民发现他时,他已跑进了海里,幸亏发现及时,浑身湿漉漉的他被好心的农民拖了回来。
变得谨言慎行的老蒋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很亲近,说话显得放松、随和。他知道我来自工厂,曾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就饶有兴趣地与我聊起了文艺创作,这是他的长项,他曾担任过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他特别爱听我讲一些工厂里工人们的喜怒哀乐,他对工厂生活很陌生,但对工人生活状况很关心。“文革”时期常有人因言招祸、因文获罪,但他对我却不存戒心,会放开谈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对一些极“左”的社会现象摇头、叹气。偶尔谈论到时局敏感话题时,他会戛然而止,我们哑然相视,沉默一下,转个话题又聊开了。我当时为了辅导轮训班的学员,正在攻读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常常向他讨教一些深奥难懂的理论问题。他十分认真,有问必答,介绍一些历史背景和大纲精要,有时也会歉意地说“我也没读过”,或者推荐我去看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四人帮”粉碎后,老蒋如沐春风,喜形于色,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但他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和所受的委屈。他当《新民晚报》总编辑的那段历史,我是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才知道的。
1977年6月17日,我到《辞海》语词组拜访赵超构先生。当赵超构先生知道我来自市五七干校时,就谈起了蒋文杰。上海解放初期,赵超构先生和蒋文杰在《新民晚报》共事,赵任社长,蒋任总编辑。抗美援朝时期,蒋文杰被派往朝鲜战地采访,他写了多篇“战地通讯”,采访了金日成将军,回国后将16篇战地通讯汇编成《卡亨几》(朝鲜语,意思是一家人)一书,由新民报上海社出版。赵超构先生还告诉了我一段轶事:1956年,市委宣传部要调走蒋文杰,赵超构社长当时正在设想把《新民晚报》扩展办成大报,他想趁《文汇报》“拆墙”风波之际,拉一些《文汇报》的人到《新民晚报》来。赵超构先生说:要办成大报,共产党员要多一点,我是民盟成员,蒋文杰是党员总编辑,我想一定要留住他,为此还专门去找了时任宣传部部长的石西民同志“吵”了一下,结果还是没能留住。
五七干校的后期,整个社会都在拨乱反正之中,我们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要编写一本被马克思誉为“我们的哲学家”的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的书。老蒋重新拿起了著书立说的笔,他被明确为编写此书的两位负责人之一,我是参与编写的成员,老蒋严谨的治学作风和高尚的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狄慈根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一位德国制革工人,恩格斯曾称他“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列宁在纪念狄慈根逝世25周年的文章中写道:“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撰写这本书,在当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老蒋带领我们不分昼夜泡在图书馆和资料室里,没有休息天和工作日之分。我们在马、恩、列全集和浩瀚的历史资料中觅寻约瑟夫·狄慈根的点滴线索,哪怕发现片言只语,大家都会欣喜若狂,相互转告。上海外国语学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编辑室的同志协助我们翻译狄慈根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以及狄慈根生平年表和一些片段资料。
五七干校的蚊子又大又凶,是我们挑灯夜战的“劲敌”,叮得人心烦意乱,点上一盘驱蚊香不奏效,得点上两盘、三盘。蚊子倒是不叮人了,但人也被熏得昏昏然。三五成群的蚊子被熏倒在地上,看似死了,一阵凉风掠过,又飞了起来。老蒋与众不同,为保持头脑清醒,他不点驱蚊香,敞开窗子,两只手臂套上长长的袖套,拳头缩在袖套里,只露出翻书、动笔的手指头,长裤脚管塞进了半高统的胶鞋里。昏暗的台灯旁一杯浓茶,这茶是他安徽歙县老家的,头上冒着汗,依然专心致志伏案工作。
半年后,在老蒋指导下,《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一书如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不少章节是老蒋执笔写的,他还是全书的统稿人,在署名时他却悄然消失了。他说:前言、后语都不要写我的名字,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还是署名“编写组”吧。
1977年年底,老蒋调任市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我也被选派到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三部参加理论班学习,学期一年。我们接触和见面的机会少了,但联系仍未中断。跟随老蒋一起从市五七干校教研组调到市委研究室工作的周伟洋跟我说,老蒋重新复出后,还是不变的风格,依旧耿介,不观风察色,不阿谀奉承,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秉笔直书,曾经有一次为文稿气得扔掉了手中的笔,这是刚正不阿的老蒋气愤之极时的发泄。
在老蒋81岁高龄时,周伟洋匆匆找我:“你能关心一下老蒋吗?他家没电梯,如今上下4楼已十分吃力了。夫人虞雅兰想去找领导,他得知后大发脾气,说‘我就是死在4楼,也不许你去找领导反映’。”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老蒋的家我去过多次,却从未注意到,老蒋也从未说起过。我很歉疚,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几经周折,终于把他的家置换到了底楼。
老蒋离休后的生活是默默无闻的,他不喜欢交际,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把晚年的时间更多地用来思考和写作,用他一生坎坷的革命经历和忧国忧民的深邃思索,凝结成5本针砭时弊的杂文集:《当代杂文选粹——虞丹之卷》《做官与做人》《刀与笔》《聚沙集》《虞丹集》。在这些集子里,他深刻反思了“文革”的教训,辛辣批判了党内种种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恶习,热情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公仆精神和老一辈知识分子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傲然风骨。“虞丹”是老蒋晚年常用的笔名,“虞”取之于他的夫人虞雅兰之姓,“丹”取之于他的女儿蒋丹丹之名。老蒋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深义重的好丈夫、好父亲。
老蒋生命的最后几年,被呼吸道、心血管、内分泌系统等多种疾病缠身,长期卧床。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耳朵几乎听不见,但脑子依然很好。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高兴,我们通过笔记本来交流,他说话,我写字。有一次,我和妻子一起去探望他,问起病情,他皱眉默然,写了“苦不堪言”四个字,我们非常难过,却又无言相慰。即使如此,他仍然十分关切社会热点问题,当我告诉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的一些情况时,他面露笑容,兴奋起来,讷讷地说:“国家有希望,国家有希望……”当问及他个人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关照的时候,他艰难地摇摇头,从床头边拿出一本出版不久的新著《虞丹集》,颤巍巍地在扉页上题写“云耕同志指正 蒋文杰”,赠送给我,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本杂文集。不久他就去世了。
他去世后,我怀着复杂的感情把这本书内60篇杂文细细地读了一遍,用红笔在书上划下了很多杠杠。我非常理解老蒋,红笔划着的每一句,都是他忧国忧民的心里话。集子里的第一篇是老蒋的“自序”,作此序时老蒋已93岁高龄,全文约千字,记录下了他早年的成长过程,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他在“自序”中称鲁迅是他“灵魂中供奉的圣像”。他写道:“鲁迅影响了我的一生。作文学鲁迅,做人同样学鲁迅。在鲁迅思想指引下,我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走上反对蒋介石政权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几乎可以说,在我倦怠时,在我遇到挫折和受到委屈时,在我被击倒在地又被踏上一脚时,棒喝我的,鼓舞我的,支撑我的,总是鲁迅的声音:‘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自序”的结尾,他自谦地写道:“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可以当个小兵,用笔。回顾我的一生,也就是在笔阵墨垒中当一个小兵。”
今年是蒋文杰先生100周年诞辰,我想用他“自序”结尾的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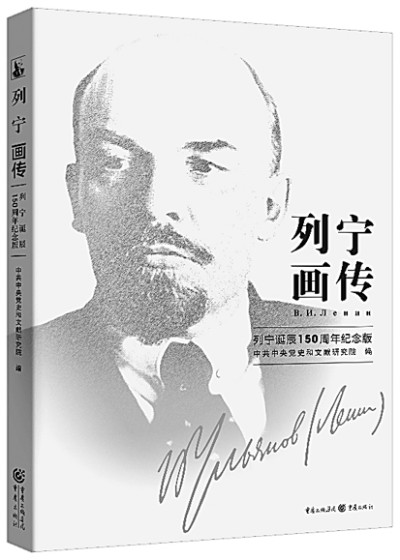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