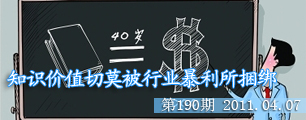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最高法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从严惩治,从严执法”,严惩性侵幼女、校园性侵等行为。《意见》共34条,通篇体现“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导思想,着重从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两个主要方面做了规定。(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0版)
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最高限度保护”,对性侵幼女犯罪实施“最低限度容忍”,这是人类社会的底线共识,也是各国法律的共同选择。但在我国,强奸猥亵幼女犯罪却呈现泛滥猖獗的态势,诸如官员“嫖宿”幼女案和校园强奸猥亵幼女案,无论犯罪情节还是相关判决,往往呈现出只有更骇人没有最骇人的态势。比如,云南大关县官员郭玉驰强奸4岁幼女,当地法院一审判决竟然只判5年,且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高限度保护”也好,“最低限度容忍”也罢,如果法律纸上说得到,司法实践做不到,不仅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极大伤害,更是对强奸幼女犯罪的变相纵容。之所以很多犯罪分子能够轻松逃脱法律制裁,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强奸幼女犯罪的认定条件上复杂至极;殊不知,认定条件越复杂自由裁量空间就越大,给犯罪分子留下的法律后门就越多。
与未满14岁少女有性行为如何定性?在以前,这首先要看是否有“暴力、胁迫”等情节;如果是有钱财交易的自愿,那就不是强奸而是“嫖宿幼女”。此外,最高法曾出台司法解释称,“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最后,犯罪男子年龄也很关键,因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看,如此之多的条条框框,看似界限分明,实则为有权有势者预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法律后门。其中,最受舆论诟病的就是嫖宿幼女罪,而“使用”这个罪名最多的,似乎就是公职人员。试想,在一个连“嫖宿熟女”也禁止的国家,出现“嫖宿幼女罪”的法律规定,该有多么荒唐?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这些年不绝于耳;这次的《意见》依然没有废除,但是规定“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界限”。
问题是,“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真的就能在事实上架空嫖宿幼女罪吗?如果幼女没有被人强迫卖淫,也不是犯罪嫌疑人以金钱财物引诱,是否仍然可以嫖宿幼女罪来判处?在大多数国家,凡是幼女在法定年龄之下,不管有无钱物交易,不管是否自愿,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一律界定为强奸。为什么我们仍旧要“谨慎”地保留那么多法律后门?
性侵幼女犯罪的罪与罚,应该站在保护幼女的角度来考量,而不能总站在男权视角替性侵者“着想”。包括嫖宿幼女罪在内,性侵幼女的法律后门都应尽数废除;无论手段与过程,只要与未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行为,就理应被视为触犯了强奸罪,这才是真正的“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