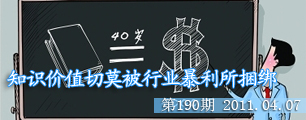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今年的博鳌论坛上,结构性改革再次成为关注热点之一。实际上,早在2012年的博鳌论坛上,世行行长佐利克就多次强调“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看重结构性改革,这样才能推动未来增长”。
我们看到,顾名思义,结构性改革就是指并非全面改革,而是有重点选择、有先后顺序的改革思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扩张“猛药”再次成为拯救各国经济“兴奋剂”,而在其负面作用逐渐显现之后,全球又陷入对于中长期失衡的担忧,并且纷纷提出结构性改革的理念。2011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提出,美国经济的重点将必须转向财政改革以及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改革。而在欧债危机的困扰下,欧盟的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顿一样,逐渐成为其新准则,其实质都是为建立一个更稳定的财政、金融体制,并以此作为经济复苏、重塑增长以及缓解失业问题的先决条件。由此看来,结构性改革的提法虽然有一些共性特征,但在不同的经济体背景下,也被赋予了五花八门的内涵。
即便在我国,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如林毅夫教授认为,结构性改革一般就是降低工资、降低福利,金融机构去杠杆,原来过剩产能消化掉。而张卓元教授则强调,结构性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在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中,则隐约看到所谓结构性改革,蕴含着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新型城镇化、经济结构调整等理念。
从根本上看,我们认为结构性改革需要依次达到如下几个目标。首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前各方对我国经济诟病的焦点之一,在于高额债务融资支撑的实体经济低回报率,呈现出一定的不可持续。因此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可维持”,这就需要真正促进生产率与实体部门效益的提升。
其次,结构性改革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双重性”,它着眼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长期性问题,但却又属于过渡性策略,是为了“治病”,与西药的短期疗效相比,它更像是中药的长期调理。就此而言,结构性调整必须承担一定风险和压力,使得经济病体感到“良药苦口”,真正使改革对象“感到难受”,才能达到效果。在此“治病”过程中,社会利益再平衡可能比增长更加重要一些。
最后,当经济“肌体”恢复正常时,才应面对寻找新增长点的问题。这也是全球的共同难题,在令人振奋的信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时期过后,除却金融与地产狂热的拉动,各国都短暂面临新增长点的“缺位”。对我国来说,寻找新增长点的过程可能是长期的,此前要避免“病急乱投医”,以及政府战略性干预的“多做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