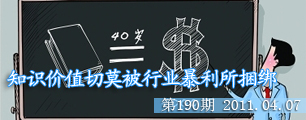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任何一个时期,文艺批评都须恪守客观公正的最高原则。作家张炜曾说:“我们对一部作品可以不谈,但不能把糟糕的作品说成好的作品,这是我们的基本底线”。然而今天,最高原则的退据失守一定令他失望,准确地说,文艺批评也许忘记用最后的沉默来表达拒绝的尊严。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这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所写的话,用它来描述当下文艺批评的状况,并不为过。
在文艺界,这样的场景似乎并不陌生:一出剧作问世,一些观摩会、座谈会便接踵而至,“大师”、“绝唱”、“高山仰止”、“辉煌史诗”的溢美之词扑面而来。对文艺家,这样的景象几乎见怪不怪:一部新作出炉,一批充满阿谀、奉承的评论文章便蜂拥而上,“力作”、“经典”、“流芳百世”、“名垂青史”的重磅评语数不胜数。
创作与批评俨然成为孪生兄弟、双子星座。在新书的腰封上,我们看得到文艺批评的深度阐释;在新片的花絮里,我们听得到文艺批评的卖力唱和;在新剧的发布会中,我们看得到文艺批评的躲闪腾挪;在新戏的研讨会上,我们听得到文艺批评的巧舌如簧——在大大小小的文艺创作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文艺批评如影随形般地鼓噪喧嚣,从难点答疑到热点聚焦,从审美感悟到学科建设,文艺批评无所不能、无孔不入,“走穴”的文艺批评越来越多,“赶场”的文艺批评越来越滥,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溢美现象汹涌成灾。不知从何时开始,文艺批评演变为文艺表扬,文艺表扬退化为文艺吆喝,文艺吆喝沦落为文艺交易。狄更斯讥讽的那个场景,正在幻化为真——在一个无法分辨好坏的语境下,“最坏”遮蔽了“最好”的存在;在一个俨然诚信扫地的氛围里,“欺骗”取代了“诚信”的面孔;在一个价值已经迷失的时代中,“黑暗”吞噬了“光明”的气息——一种新型的文化贫困正笼罩在文艺批评之上。
文艺批评缘何变成文艺表扬?答案也许并不复杂,人情的传统、权力的寻租、价值的迷失、心态的失衡、利益的绑架、原创的不足……这些造就了文化建设的好大喜功,也造就了文艺批评的虚假繁荣。在各种文艺创作现场,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文艺批评不再是在相互辩诘中彼此促进,而是借助肉麻吹捧,自说自话;文艺批评不再是在相互交锋中认识真理,而是捞取名声资本,哗众取宠;文艺批评不再是在相互砥砺中辨别是非,而是变得顾影自怜、故步自封。文艺批评的时尚化、边缘化、口语化、散文化、纪实化、低俗化,批评家对于重大文化现象的缺席、缺位、失语、乱语、无序膨胀,使批评载体滑向媒体化、口号化、红包化、核心刊物化,这些是文艺批评丧失生命力、降低文化品位的重要原因。大大小小的文艺圈子不仅在分割领地,更在瓜分利益;愈来愈狭隘的文艺批评正在变成少数人的交易专利和交际工具。
文艺批评本是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借助文艺学剖析文艺或借助文本探讨文艺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使用习惯上来看,“批评”包含着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批”与“评”。创作与批评,归根结底是一种架构于相互信任之上的价值判断,文艺家因为信任建立了与批评家的阐释关系,受众因为信任建立了与文艺家和批评家的鉴赏关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艺批评已经丧失了这种基本的文化自觉和道德自律,从狭隘的个人需要和利益驱动出发,表现为一种热热闹闹的肤浅,创作、受众、批评之间由此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
“人类文化上的每一小步,都是通向自由的一大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上文化的昌盛也总是伴随着批评的活跃。批评的繁荣会将社会引向光明,批评的萧条则会让社会滑向黑暗。曾有学者反思,何以20世纪早期文艺界出现了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的生动局面?应归功于当时尖锐的文艺批评、激烈的文艺争鸣。正是在这种批评和争鸣中,一个又一个新学说纷纷涌现,一个又一个文艺家亮丽登场。然而今天,我们的文艺批评,不再有循循善诱的耐心、拾遗补缺的宽厚,更不再有秉烛观幽的洞彻、怒剑出鞘的锋芒,文艺创作的勇气和风骨,正在文艺表扬的温柔乡里慢慢消融。
其实,文艺批评不仅是一种人文学科,更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对于天地生死的追问和呈现,关乎命运,关乎心灵,关乎情感,关乎希望,更关乎民族和未来。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在遥远的德意志联邦,93岁的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辞别尘世。他的离去让整个德国唏嘘不已,包括德国总统在内的数百名社会政要、文化名流自发为他送行。在德国,这位挂满勋章的批评家是德国文化的“孤本”,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面孔众所周知,一位小说家甚至用一句笛卡尔式的话来赞誉赖希—拉尼茨基的地位:“他评论我,所以我存在。”可以说,对于德国来说,赖希—拉尼茨基的存在,不仅是文学的一面旗帜,更是文化的一颗良心。
期待我们的文艺批评,葆有更多这样的旗帜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