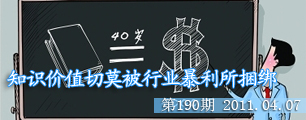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我的父亲曾是村里第一批外出打工谋生的年轻人,他走出村庄的时候是80年代末。父亲外出务工的营生,是挖钨砂。在贫穷的赣南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稀土资源和钨矿资源——这两种矿藏在军事工业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被称为“白金”和“黑金”。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无论黑白,换来的都是比种地要来得多、来得快的真金白银。
作为第一批外出“淘金者”,那时的荣光大抵可以想象。我们家率先添置了“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当大家还要冒着烈日种收稻子交公粮、以工代赈节省口粮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步入了小康。
不过,时机再好,都敌不过造化弄人。正当父亲春风得意时,灾难突然降临——有一次,他在烤火时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双脚在昏迷中被通红的煤球烧伤。幸亏被人及时发现,命总算救回来了,但脚却落下了残疾。
脚受伤了,通往村庄外面谋生的路也就断了。虽然避免了截肢,却也花光了那些年“淘金”攒下的积蓄。被灾难打得破败不堪的生活如何继续?
腿脚不利索,下田、挑担肯定不行了。于是,父亲指望着能在乡里的集市上寻找营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曾经做过修鞋匠,一针一线都是为了让因变故而风雨飘摇的家庭更加稳固。可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再也不会留恋一双破鞋,修鞋匠生存的空间,越来越逼仄。
后来,父亲改行摆起了卖烟丝的小摊。几张木凳、一块门板,往街市的屋檐下一摆,就是一份营生。对顾客来说,雪白的卷烟纸、金黄的烟丝,燃烧起来就像驱除烦恼和焦虑的迷药;而对于父亲而言,它们却是为了生活的灶膛能够每天冒起炊烟。
那时候的集市还很和谐,几乎没有管理者和底层谋生者的对立和冲突,这或许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城管这个职业。工商所、税务所的工作人员上午会在街市游荡一圈,每个摊贩收个五毛一块的管理费。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实在没有钱也就算了,绝不会踢摊伤人。
如今的街市,恐怕再也没有这么宽松的谋生环境。每个底层谋生者,都显得战战兢兢。管理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常常带有“洁癖”,往往容不下一个破败的小摊。以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看不到这个破烂小摊里承载的平凡生活,看不到这个破烂小摊里寄托着的希望;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通往光鲜政绩路途中的拦路虎。这种冷血的态度和机械的治理方式,让熙攘温情的街市,慢慢变成了政绩与生存对抗的战场。
到最后,集市被美化了,路边摆摊的几乎绝迹,农家人卖些自家种的蔬菜,也必须到农贸市场里去。而农贸市场的摊位,都是出租的,无论有没有生意和利润,都得先“买票”再入场。
集市上谋生难了,父亲回到了村庄,帮助母亲耕种那些被荒废的田地。村庄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很多田地都荒芜了,但对“留守”在家的父亲来说,种田的老本行终究是农人的一种生计。如果赶上好年成,加上谷价见长,到了收获季节,不仅能从地里收割全家所需的口粮,还能有一些富余的收入。
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劳力的流失,在农村打零工的价钱也上升得很快。随着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拆老房子、修大马路都需要人手,但在农村却几乎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村驻守的劳力,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吃香。后来,父亲便带着母亲,在农闲的时候去打点零工,挣些外快。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子。在乡村,父亲营生的变更,某种意义上而言,或正是农村变化的侧影。他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因为苦难而绝望,至今为止,土地也一直给他生活继续的机会土壤。因为有了土地的厚重,再苦难的生活都能孕育希望,甚至开出花来。只是不知道,城镇化把农民赶上了楼,让他们悬空于土地上,脆弱的生活又该去哪里寻找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