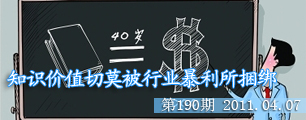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最近在读一本新书《错案》,作者勒内·弗洛里奥,一个法国律师。
法治成熟的国度仍然会有错案。勒内·弗洛里奥在书中苦口婆心地劝导法官,“我们不应该把已经掌握的罪证放在天平这一端,而把可疑的材料放在天平那一端,然后把其中较重的一端当作结论”,“怀疑应该导致无效,因为,毁损一个无辜者的名誉,或者监禁一个无罪的人,要比释放一个罪犯更使人百倍的不安!”
与之相印证的是,基于几千年来深植于血脉的“严刑峻法”律令,和对有限的刑事侦查技术和能力的心知肚明,面对从重从快的政策和“命案必破”之类的口号下起诉的案件,法官狐疑于侦诉缺陷和瑕疵之余,心底犹豫着“疑罪从无”,对某些“疑罪”却不得不按下“从轻”或“从挂”键。左右下判的,还有面对案卷“应该是他”的内心倾向、“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大局考量以及“放纵犯罪”的政治和舆论重压。
我曾不止一次的感慨,当下国人甚至是一些司法从业人员对法律的信仰,还停留在拜“送子观音”的功利阶段,纵然脸色虔诚口中念念有词,一当真就被视为迂阔。真正激起对良法的遵从和渴求的,往往都是在得偿所愿或痛定思痛过后。
对刑讯逼供这一“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被新刑诉法纳入庭审必经程序,但回溯既往,要确信侦查中没有过刑讯,未免太过天真。自古就有“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之说,包青天惊堂木一拍,棍棒下出“刁民”也出罪犯,这是传统司法心照不宣的法则。记得上世纪末,某地连发两起投毒案,庭审时律师都将刑讯逼供作为辩护理由,那时候核实是刑讯问题,多是由侦查机关盖公章出“条子”自证清白。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在审理第二起案件时,也许是之前被问得很烦,刑警队出具了一个大大咧咧的便条,“本案我们汲取了×××一案(即前一案)的教训,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法官傻眼了,这岂非自证前一案确曾有过?
疑罪从无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在长期以侦查而非庭审为中心的中国式法庭上,法官,乃至法官背后的法官,仅有怀疑是不够的,这意味着所谓“公安做菜、检察端菜”的流程环节中出不得任何一点差错。但这貌似是不可能的,那些“办理千案无一差错”的圣徒式模范,只存在于高大全的拔高宣传中,并非现实司法的常态,否则没人敢办案了。
陈年痼疾堆积形成的壅塞,需要大开大阖的冲刷涤荡。刑法发展到修正案(八),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已成天下大势,无论是立法理念的进步,还是司法导向的调校,这其间,既有法治清明的路径认知,更有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这些年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词汇逐渐淡出裁判话语,纵然是寒气凛冽的定罪判决,也愈来愈多冷静的证据分析和“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司法温情。
今年以来的刑事司法领域,一些被纠正的冤假错案被媒体相继披露,一批长期挂账的“疑案”密集进入各地法院“审判季”,中央政法委适时出台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向“以庭审为中心”转型,大法官沈德咏的文章《论疑罪从无》一石激起千层浪……“疑罪从无”,你,终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