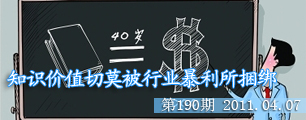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1963年,海峡两岸两位作家老舍和余光中关于散文分别说过这样两段话,“我想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文化普遍提高,人人都能出口成章,把口中说的写下来,就是好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两位作家的文章题目既扣主题又很有趣,《散文重要》,《剪掉散文的辫子》。散文家族庞大,宽厚大度,海量包容。体裁繁多,风格各异正是散文力量之所在。我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分类,源远流长,其间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博到约的过程,最多时曾将散文分为一百多类。由于植根于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再兼之国外的推动或说横向引进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在最初的发展中,散文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的。用一位学者20多年前的点评,现代散文崭露头角时便已是一位成年人。
如今图书市场上散文作品的繁荣自不待言,用途广,与生活联系密切,而且生性少拘束,无需刻意加工,自然受到创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兼收并蓄使得散文队伍借助现代传播手段不断壮大,正如王佐良的乐观预计,“看来口头、笔头、书本气、电声化、群众爱好、个人趣味等等会并存一个时期,各自发展下去,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易学难工,木秀于林,散文的写和读同时最大范围地暴露在功名利禄的侵袭下,被剥蚀得遍体鳞伤,苦不堪言。充分构思,精心安排的推敲和思量愈来愈少,超凡脱俗,出神入化的品格和魅力越发难寻。代之以琐碎絮叨,浅薄无聊,故作高深,掩饰无知,装扮伟岸,附庸风雅,俯拾皆是,不加选择,堆砌其中的脂粉气,裹藏于内的市侩气,不一而足。你不能不佩服一些人的精明,市场看好什么,国际流行什么,形势要求什么,全在他们的胸中,森罗万象,吐纳自由,好不自在。刚刚对自己的文章被砍得“不成样子”发完牢骚,掉过头来便追风逐利,迎合时尚,一而再,再而三地“拼接”个人作品,同时又赞叹起出版方眼光之独到高明。每本集子前言后记、提要宣传,都有千万种理由,不愁不让读者动情爱怜。林林总总,花花绿绿的新作选集,大多是缺乏新意的重复出版,作者、印行者都把“编排”艺术做到了极致。颠来覆去的几道菜,藏头裹尾,层层包装,只能糊弄一时一地,长此以往,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最终必然令人嗤之以鼻,过量生产,速生速朽,了无痕迹甚至留下恶名。
也许有人会反驳,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喜欢散文直接切入主题,不枝不蔓,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已是明日黄花。其实不管外在环境如何纷纭,锤炼自己的内心,抱持可贵的敬意和诚心,把好奇、执着和关怀尽量结合得紧些,再紧些,总归是为文创作的正途。没有深切的情感和独到的见识,写出文章来肯定匮乏新颖有趣的东西。最好不率尔操觚,苟且下笔,个人省点纸墨精神,社会免得灾梨祸枣。没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沉潜琢磨,切莫拉开架势,哗众取宠,假模假式地摆布炫弄自己。突出的一例即是,大量游记探访文章充水勾兑得如同肿胀的旅游说明书。放任自流的鼓噪声里,铺天盖地的捧杀式批评中,回味纪律和责任的意义尤为重要。
文学的纪律是内在的节制,文学之所以重纪律,为的是要求文学的健康。梁实秋提出的观点曾被认定为文化精英主义,我们认为贴近平民百姓和生活实际与之并不相悖。“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情感和想象,同样离不开理性的驾驭。反之,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思维丧失了活力和弹性,语言没有了敏锐和灵性,绅士气才子气甚至流氓气肆虐横行,粗鄙虚浮之文遍地,文质彬彬之作只好逃遁隐身。
俗套陈言味同嚼蜡,故弄玄虚浪得名声,堂而皇之地兜售货不真价不实的假冒伪劣作品,中饱私囊者令人作呕。面对智者先贤、佳作名篇,他们竟也不知汗颜。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不在乎能写多少,而在乎能把多少不写出来;放纵地跑马占荒尽量少一些,节制地精雕细刻尽量多一点。巴金在《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后记中披露自己的座右铭,是一帖文坛的清醒剂,“‘决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不管写什么长短文章,我时时记住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