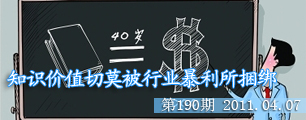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古文简洁,但简洁有时会带来歧义,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读,《论语》里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便是典型一例。
据杨伯峻《论语译注》,这句话的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这里,“攻”作“攻击”解,“已”作动词“停止”解。
然而,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解释,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把“也已”作为语气词,于是这句话就译成“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正好与杨译相悖。李泽厚认为,“这可以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
还有学者把“攻”解为用功的“功”或治学中的“治”,又带来第三种解释:学习异端邪说或从事于不正确的学术研究,是有害处的。
最有趣的理解也许来自著名英国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他在英译中认为这是以织布作喻,“攻”作“织”解,“异端”指“不同的线头”(different strand),于是有了这样的英译:织不相干的线头,毁了整块的布。(He who sets to work upon a different strand destroys the whole fabric)什么意思?大概强调要心无旁骛从事仁道吧,接近第三种解释。
翻译大家傅雷说,“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威利翻译之奇,也许正是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表现。《论语》里还有一处提到,孔子向卫国大夫遽伯玉的使者问起蘧伯玉近况,使者说其“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想减少过失却尚未做到。
古文简洁带来的歧义,在某种程度上也丰富了古文的思想内涵。上面的几种理解似乎都有道理,不管孔子的原意如何,这些说法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影响,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喜好来取舍了,当然也不妨绞尽脑汁,再创一说。其实,古人之所以能“六经注我”,正有赖于文字歧义带来的模糊空间,像康有为就通过注《论语》将一心“梦周公”的孔子改造成维新变法的“教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