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振川 受访者供图
他的父亲是长安画派的奠基人,他是长安画派的“扛旗人”,父子俩演绎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他说,到生活中去犹如泡酸菜,三番五次地体验,才能谈得上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才有可能画出这个地方的味道。
“到生活中去犹如泡酸菜,菜需要浸泡在菜坛中一段时间方可变为酸菜。如果只是在酸汤中沾一下就拿出来,菜是不会酸的。深入生活也是这个道理,到一个地方去写生,也需要待一段时间并尽可能再次下去,三番五次地体验,才能谈得上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才有可能画出这个地方的味道。”满头银发的赵振川,在艺海中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写下了上述艺术箴言。
赵振川生长在一个艺术之家,其父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奠基人,其弟赵季平是著名作曲家。孩提时代,赵振川曾一度住在西安碑林的院子里,石刻、碑文、造像,秦汉唐宋的古老遗存在一群孩子的嬉戏与吵闹声中显得格外宁静。1962年,中专毕业后的赵振川决定学画,师从著名画家石鲁。
赵氏父子对“长安画派”相继作出突出贡献,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贾平凹曾经这样评价赵望云、赵振川父子对中国画艺术和长安画派的贡献:“仰着望云,一喊震川。”
一幅泛黄的画作已摆放在赵振川画案上多年,这是父亲赵望云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农村写生集》系列作品中的一幅。在这幅题为《为衣食之奔忙者》的作品中,手推独轮车、肩扛重物的一路行人佝偻着脊背,蹒跚向前,加上寥寥几笔枯树矮屋,勾画出那个年代的劳苦大众为了生计而奔波操劳的场景。赵望云长期致力于“农村写生”,一直实践中国画革新,关注民间疾苦,“从不画不劳动者”。
父亲的经历和教诲深深影响了赵振川。不到20岁,赵振川就跟随父亲到甘肃等地写生。1964年,赵振川在父亲的支持下,到陕甘交界的陇县下乡。八年间,赵振川把乡间的农活都干遍了,而且都干得还不错。不变的是,担水拉煤、种菜养鸡之余仍坚持写生。
经过八年的“生活浸泡”,赵振川磨炼了意志,提纯了灵魂,也真正理解了“生活”二字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此后的岁月中,他始终秉承父亲“面向大西北”的创作理念,并用画笔追逐着父亲的脚步。从陕北的安塞、延川到陕南的西乡、紫阳;从兰州、敦煌到乌鲁木齐、伊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赵振川在大西北的山川中留下了艺术的足迹,先后创作出《戈壁春居》《天山牧歌》《黄河之滨多枣林》《祁连山放牧》等一大批饱含着充沛的生活气韵和活力的中国画精品。
赵振川曾送给作家陈忠实一幅国画,也取名《白鹿原》。“从他的画里似可嗅出民间生活烟火气味,感知世道与人心。这一点不仅超凡脱俗,而且注定了画作的生命活力,也呈现出独禀的个性气质。”陈忠实这样评价赵振川的作品。前者写出了小说《白鹿原》,用文字记录下了关中生活的烟火气,而后者用绘画的方式实现了同样的目的。殊途同归,画家与作家在心灵层面上完成了一次激情的碰撞。
赵振川常跟学生讲,作为画家,读书少不行,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了解少不行,但最要紧的还是生活的积淀,对山川不了解,对黄土高坡不了解,没有在生活里“泡”,再有思想也不行,即所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张萍跟随赵振川学画多年,她介绍说,跟赵振川去写生,他不仅要求学生去看去画,还要跟他一起到农民家里去,跟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收成和生活状态,甚至到马厩、牛栏里去看看。
王归光也是赵振川的弟子。赵振川曾跟他说,绘画是艰苦的职业,既要勤奋,还要能耐得住寂寞,是谓“寂寞之道”。有一次,他去看望赵振川,一进门就进入了一个“画”的世界。床底下压着厚厚的一层作品,足有一二百幅,画案上还有百余幅,另外还有一大摞未完成的墨稿在画案的另一端。“赵先生出身名门却从不懈怠,他现在的艺术造诣之深绝非偶然,实为勤奋的结果。”王归光感慨地说。
作为当代长安画派的“扛旗人”和灵魂人物,赵振川重担在肩思己任,经年累月笔耕勤,不仅潜心塑造了西北山水新容,更致力于带领众多弟子不断发扬长安画派精神。为了发展壮大这一事业,赵振川积极培养长安画派接班人,就连从事设计工作的儿子赵森都被他拉来“入伙”,一起“泡”在艺海中。“最难忘的是他没有周六周日,平时都在画画,甚至大年初一也在画画。并且要求我也如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给自己留了个周日。”赵森无奈地笑着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赵振川认为,中国的艺术家要“守住笔墨的底线”,创新不能远离民族传统艺术的本体,试验更不能离开生活的土壤,这也是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方法论。
由于成就斐然,赵振川被评为陕西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如今76岁高龄的他,担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及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虽然职务很多,工作繁重,但赵振川仍不忘父亲“到民间去”的嘱托,一有空闲,他就会到秦岭、渭北和陇山一带去转一转,去“泡一泡”,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作者:王钊,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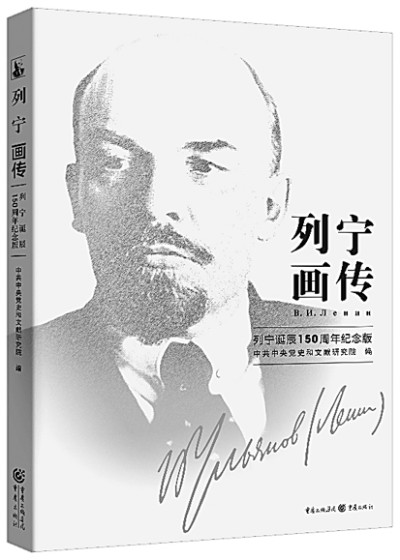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