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实行过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开放或闭关政策问题,一直有很大分歧,聚焦点之一就在明朝时期。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史学界对开放与闭关的概念理解不一,不仅在认识上存在差异,而且缺乏综合考察和对比分析。明朝出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表面上将政治目标设定为全面“复古”,但在对外交往实践上并不泥古僵化,而是有所创新。
“复古”外衣下的明朝对外政策
(一)以“不征”为基调的中外关系
中国历史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而是奉行“王者无外”的天下观。明初,朱元璋也曾效仿前朝,派出使节前往周边各国宣示正统,以确立自己的天下共主地位,延续传统的封贡模式。但在具体政策导向上有两个明显变化。
一是在事实上推出了自己的天下观。传统的天下观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边界。朱元璋心目中的天下则实现了从无边界的“天下”向有范围的“天下”——即中国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明朝与邻国之间开始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意识,即“各守疆界”。洪武四年九月,朱元璋曾训示诸臣:“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在晚年的《皇明祖训》中,更明确提出“不征之国”的概念,并将朝鲜、日本、安南等国列为不得征伐范围。
“不征之国”的出现以及对邻邦内部事务的不干涉态度,加之“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显示明朝对外政策较之前朝已经有重大变化。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事实上放弃了天子征伐之权。这一理念与元朝对外交往模式完全不同,也和西方殖民帝国的海外扩张有本质区别。
(二)不同时段对外政策调整,始终掌握外交主导权
明初的对外联系是全方位的,包括陆上与海上。明朝六遣傅安、五遣陈诚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七上北海。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拓展了封贡体系的外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整合过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构建了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
“闭关”一词,古已有之。明朝最典型的一次对外闭关政策出现于与西方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之时。正德十二年(1517)葡使托梅·皮雷斯来华,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以失败告终,加之葡人在广东的不法行为,导致嘉靖朝一度下令在广东禁绝“番舶”,严厉打击葡萄牙人在沿海的走私活动。这一政策是对古代传统的继承,即《周易》“乃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嘉靖三十六年(1557),明廷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但需承担纳税等义务。澳门始终处于明朝政府有效管辖之下。澳门开埠,标志着明朝打开一个对外的窗口。
晚明时,西班牙、荷兰乃至英国都曾先后尝试对中国展开包括武装侵袭在内的殖民活动,但无一例外地被击退(仅台湾岛因为重视程度不足,一度被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占领)。最为典型的事件是发生于崇祯十年(1637)的英国船舰闯入虎门事件,即中英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中外档案证实了当时英国从海上以武力打入中国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印证了直至17世纪中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相较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明朝政府始终掌握着外交的主动权。
(三)有海禁,有局部闭关,但从未“锁国”
明初,由于倭寇侵扰,流亡海外的敌对势力很多,以及海防建设尚不完善等原因,曾实行海禁政策。但海禁和禁止对外国交往不是一回事。
第一,明代的海禁政策针对的是本国人民,目的是切断敌对势力从大陆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更不是有意识的闭关锁国。
第二,在海禁政策实施期间,明廷把敌对势力留下的大批航海人员收编到军队中,在很短时间内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近海巡航保障了海上活动的正常开展。
第三,虽有海禁,但并不禁止正常的海上生产活动。在个别时段,明廷确实曾牺牲局部利益,禁止下海捕鱼、商贩,但大多是临时性的禁止,更不是明朝政府的基本国策。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的宁波争贡事件,曾被很多学者视为明廷主动断绝对日交往的“闭关”证据。但爬梳史料,当时任给事中的夏言奏疏并没有提出撤销市舶司和断绝对日交流。事实上,明廷于嘉靖十八年还接纳了日本贡使来华;在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是否给予丰臣秀吉朝贡的权力仍是双方交涉的主要议题之一。援朝战争使官方外交关系一度断绝。
明朝自建立起,就有“南倭北虏”问题。与海上不同,明朝在与中亚国家交往中确实曾多次关闭嘉峪关贡道,大体上是以施压作为羁縻的手段,以维护关内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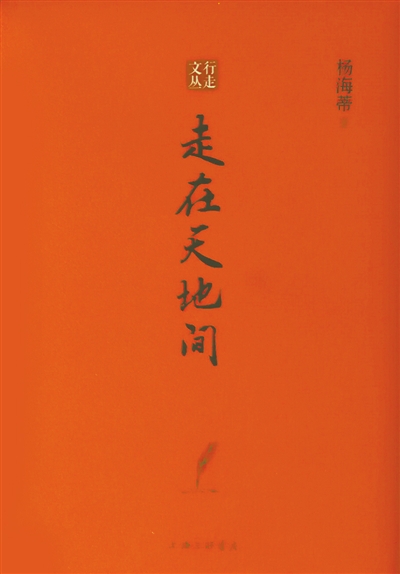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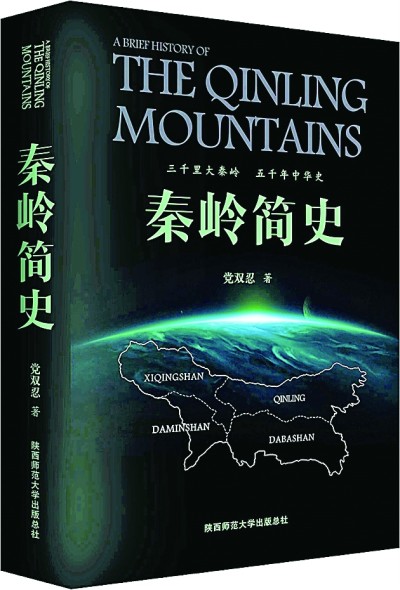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