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惩处网络技术犯罪的法律规定,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在相关新罪名的刑法条文的最后一款均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就产生了在共同犯罪的场景下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的犯罪与所支持、帮助的犯罪之间的罪名竞合问题。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行为是否应单独评价,值得思考。
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行为具有专门刑事评价的必要性。其一,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行为在符合相应罪名罪质的情况下具有单独入罪的条件,不必再依托其所服务、支持的其他犯罪进行依附性评价。刑法第286条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客观上表现为消极不作为,以致产生危害信息网络安全的法定危害后果;刑法第287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客观上表现为设立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发表制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信息,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刑法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客观上表现为,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前提下为相关犯罪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这三个新罪名都主要以网络技术手段凸显其行为特征,与其所服务、支持、帮助的特定犯罪在客观表现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行为的独立性较强。其二,在“互联网+”犯罪模式下,若以传统共犯思路追究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行为的刑事责任,刑事证明的难度较高,影响刑事处置的效率。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可以与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犯罪形成共犯关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其所具体帮助的罪行不一定符合传统共同犯罪的认定规律,在被帮助的罪行因证据等原因而无法入罪的情况下,帮助行为依然可以单独认定。刑法的修订充分因应了互联网社会犯罪治理的客观需要。互联网形态的非法使用技术行为与其他具体犯罪行为在主观上的合意内容常见为默认、许可、放任,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共同犯罪故意;客观上的共同行为表现为一方的网络技术行为是其他犯罪行为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因而即使其他罪行难以追究,也有必要专门刑事追究这种带有“助纣为虐”性质的恶意滥用网络技术的罪行。其三,在某些“互联网+”犯罪的场合,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行为对于其所服务、支持的其他犯罪而言,重要性不可或缺,也有专门追究的必要性。
在松散型共同犯罪中,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行为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和作用,应当单独定罪。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四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典型案例中,“谭张羽、张源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系较为典型的松散型共同犯罪。在缺乏明确的犯意联络和紧密的行为配合时,这种若即若离带有放任意志因素的帮助行为可直接认定为相应的非法网络犯罪罪名,单独评价有利于刑事司法有效及时处置,也符合刑法罪责自负、罪刑相当等基本原则。
在紧密型共同犯罪中,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行为是否按主罪的罪名以共犯论处须综合情况把握,不可一概而论。在紧密型共同犯罪环境下,是将非法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行为作为主罪的共犯,还是依其技术犯罪行为本身的性质继续单独认定,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例如,某非法集资公司通过线上非法吸收资金,其内部设置有专门的IT技术部门,负责建构App用于发售非法理财产品,并进行日常网络维护,该部门负责人领取员工薪资。首先,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技术部门负责人主观上明知所在公司在实施非法集资犯罪,客观上仍为其设立专门的网站,发布非法集资信息,其行为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犯罪构成。其次,作为犯罪单位内设部门负责人,日常行为与公司的非法集资行为联系紧密,与外包化的技术服务行为在紧密性上有一定差异。网络技术服务与非法集资信息发布是涉互联网非法集资犯罪具体实行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否因此就评价为非法集资犯罪,依据从一重处的法条竞合原则优先适用非法集资罪名。笔者不赞同一刀切的重罪名优先的认定思路,还是要从主观故意的内容与客观行为的紧密联系程度来分析帮助行为与主行为是否达到共同犯罪的程度。通常可根据任职时间、行为内容、获利情况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互联网+”形态下的犯罪,只有最能体现主罪行特质的那部分行为宜归集评价为主罪名,例如具体实施诈骗资金的行为,直接向公众宣传虚假理财产品非法获取、转移、使用资金的行为。不体现主罪名特质但对主罪名的罪行得以实施起到技术支持、保障、服务等作用的相对独立的非法网络技术支持行为,除非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从中获取了远超出技术服务价值的非法利益的,可依作为共犯的主罪名论处,在其他情况下因刑法对此类非法网络技术支持行为有了专门的评价罪名,单独评价更符合其行为的本质,也有利于达至罪刑的均衡。
(作者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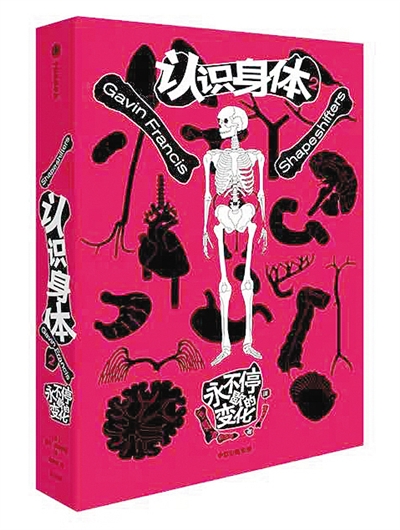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