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量刑协商、值班律师制度、认罪认罚案件审理程序等问题的充分讨论和共识达成,如何为被害人、社会治理其他力量参与合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对话平台,切实构建共建共治的现代犯罪治理模式,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这样,才能在实现合作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同时,让公正的实体正义和有效的犯罪治理,成为通往现代刑法谦抑之门的程序路径。
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发展历经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历史跃迁。其中,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生活教义是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干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和“法官只是一架法律的宣读机器”,则成为放任行政和机械司法的最佳写照。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的爆发及其惨痛教训,使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为“罗斯福新政”施行的圭臬,从而在宣告“从出生时起到进入坟墓时止,无所不在政府管制之下”的垄断行政发轫的同时,开启了以“必须保卫社会”为使命的能动司法的历史。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各种新型社会风险层出不穷,而风险治理方案本身,或者囿于问题角度的片面,或者限于学科视野的狭窄,或者困于知识结构的单一,往往在成功治理一种社会风险的同时,又隐藏着引发更大社会风险的可能。
社会治理理论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展开
在今天,正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抗击带给我们的深刻体认:只有在专业分工基础上进行跨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跨系统合作的社会治理再造,进而重塑社会治理文化,重构社会治理制度,重建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摆脱“片面正确”的社会治理迷思,有效防范和科学化解系统性社会风险。
正是基于此,自十八大提出,到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全面绘就,一场以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决策民主化、治理方式柔性化、治理空间社会化为路径、以政府掌舵—社会共治—公民自治为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我国波澜壮阔地展开。而在刑事司法领域,作为刑事诉讼私力合作的发轫和刑事诉讼公力合作的革命,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施行,既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延伸和展开,又是刑事司法改革对以恢复性司法为圭臬、以合作式司法为核心的犯罪治理现代化变革所作的回应。正如“恢复性司法”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尔德·泽赫指出,所谓恢复性司法,就是“最大程度吸纳特定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司法过程,以求共同地确定和承认犯罪所引发的损害、由该损害所引发的需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责任,进而最终实现对损害的最大补救目标。”
这种通过合作,尤其是认罪认罚从宽公力合作来处理刑事案件的模式,在我国试行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0年1月30日,笔者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2018年至2019年两年间,一审刑事裁判文书共计1915864份,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裁判文书就有387376篇。其中,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7154篇,关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81852篇,关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有2326篇,关于金融诈骗犯罪1447篇,关于危害税收征管犯罪2356篇,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553篇,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8839篇。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阔步推进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需要进一步提升完善的问题。除控辩审三方合作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合法性、有效性审查等学界和实务部门热议的话题外,笔者以为,还应关注并推动两个层面的合作:一是行刑衔接合作;二是控辩审三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合作。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和科学合作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刑事案件,大多是行政犯罪案件。虽然行政处理程序并非行政犯之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前置程序,但是,行政执法乃社会治理的第一道法律防线,而刑事司法则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法律保障。是故,包括我国在内的现代世界各国,行政执法系统无论在职能配置还是人员编制上,均远宽于、多于刑事司法系统。此其一;
其二,刑罚乃不得已的恶,能够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行政责任的追究,不实际动用刑罚,即可将被行政犯所侵犯的行政秩序恢复到犯罪发生前的状态,其实才是现代司法用刑追求的最高艺术,正所谓“刑期于无刑”。
其三,行政犯纷繁复杂,专业性强,虽然我们一直想把法官提升到一种纯粹理性领域,高于并超越那些令人不安和偏斜的“人的局限性”的约束,“我并不怀疑这种法官的理解是庄严伟大的……但是,这从来也不过是部分的真实。”而行政执法的优先处理,尤其是行政执法处理和刑事案件初查的同步进行,不仅为后续展开的刑事司法程序提供了有力的专业保障,而且因为行政执法证据的先行审查和行政不法事实在行政执法中的先行查明,成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认罪认罚的有力推动力量,进而推动控辩双方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进行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合作。这也正是笔者多年致力于倡导“行政先理为原则与刑事先理为特殊”的行刑衔接合作机制的缘由所在。
其四,行政犯在前置行政法上的法律责任已经确定乃至实现,为控辩双方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合作重心由定罪量刑并重,向以量刑为主转移,进而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创造了条件。当然,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能降低,无论行政执法证据的采信还是行政不法事实尤其是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查明,均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查认定。虽然认罪认罚的成立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及其无罪辩护权利的放弃为前提,但这绝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只有认罪的义务,而没有辩护的权利。相反,鉴于控辩双方在专业水准、法律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必须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以弥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合作能力上的不足,从而实现双方合作的实质平等。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和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反悔,则合作的基础不再,或者依法提起公诉,或者转换刑事诉讼程序审理。
被害人与社会治理其他力量参与合作
恢复性司法实践范式虽然多种多样,既有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和解模式,又有各方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协商会议形式,还有由各方利害关系人以及其他对案件有兴趣的社会成员参与的圆桌会谈范式等。但是,为案件各方利害关系人包括被害人、加害人和受害社区等提供一个对话协商的场域和机制,却是所有恢复性司法范式共同遵循的原则和做法。因为实际上,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希望通过刑事司法程序所获得的,也“远远不止是案件得到简单快速的处理或关于判处年限的讨价还价”。对于刑事被害人和受害社区,则更是如此。被害人和受害社区能否从其所遭受的伤害的处理程序中获得丰满的正义体验,既是被害人和受害社区能够从犯罪侵害中恢复和痊愈的关键,也是恢复性司法的精髓所在。而传统对抗式诉讼模式下,虽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听取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意见,但因真诚对话、充分商谈的合作平台,以及以被害人和被害社区为代表的社会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不畅,致使程序运行的透明性、开放性不足。
为此,《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第16条中要求,“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方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重要考虑因素。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听取意见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不仅如此,《指导意见》还在第35条至第38条中,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社区等社会治理其他力量的意见表达予以了明确。
因而,随着量刑协商、值班律师制度、认罪认罚案件审理程序等问题的充分讨论和共识达成,如何为被害人、社会治理其他力量参与合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对话平台,切实构建共建共治的现代犯罪治理模式,成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这样,才能在实现合作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同时,让公正的实体正义和有效的犯罪治理,成为通往现代刑法谦抑之门的程序路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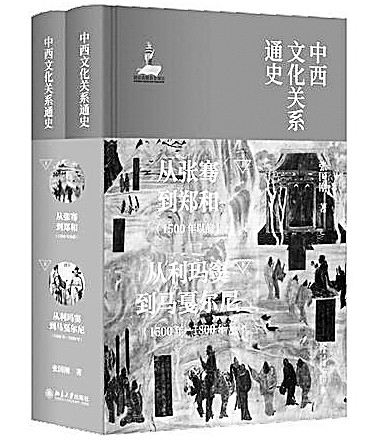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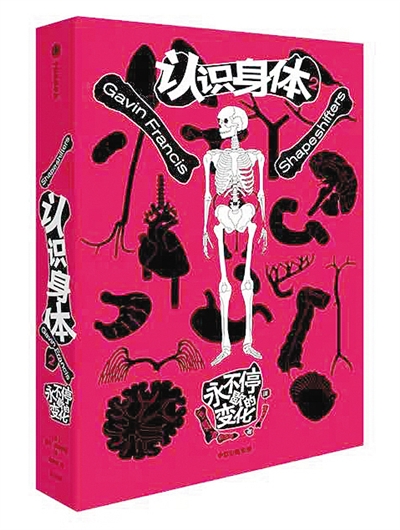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