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词出现于何时?尚无定论。但是,黄帝时期出现的法官与诉讼活动,却有记载。《汉书·胡建传》有“黄帝李法”之语,“李”即是“狱官名也”。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总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称其书曰《李法》。”后世的大理寺、大理院的“理”,其实就是由“李”转来。上古时期的诉讼活动,也有一些传说。我们在法院门口经常见到的独角兽,就与古代审判密切相关。独角兽的学名叫獬廌,简称廌,传说是一种能断案的神兽。《说文·廌部》说:“廌,獬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省。”所以獬廌也写作獬豸。
廌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是法(灋)字的三个字素之一,并且是最为核心的字素。正如《说文·廌部》所解析的:“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去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廌不仅代表了法之“去不直”的精神,也成为法律的符号和图腾。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曾获一獬豸,仿照其形制成獬豸冠戴于头上,一时成为风尚;秦汉以后,獬豸冠更被冠以“法冠”之名。一直到清代,司法官员所穿的补服上还绣有獬豸的图案。
传说最早引獬廌而为神判的是皋陶。皋陶是尧舜时期的首席法官,称为“士”,也称“大理”。《春秋·元命包》云:“尧得皋陶,聘为大理。”民国学人徐朝阳专门写过一篇《法官始祖皋陶考》,称赞皋陶“实吾国法官之始祖,吾人所最钦仰者也”。皋陶在那个时候就已具备了丰富的司法经验,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曾这样夸赞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皋陶的回答则是:“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恰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至于皋陶如何引獬廌而为神判,王充的《论衡·是应》曾有记述。
儒者说云:“觟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
我国的上古史,一向以黄帝为国史的开端,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从《五帝本纪》开始写的。所谓五帝,从黄帝开始,黄帝之后依次是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但近代疑古学派崛起,对许多古帝的存在持怀疑之论,历史学者们写上古史时,就转而以有甲骨文字出土的殷商时代为中国史的开端,夏代以前就归之于“传说时代”了。所以尧舜时代的皋陶神判,亦为传说,“属是属非,难寻确证”。不过,上古时期已经有了审判治狱,却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当时已有判决书之制,亦无可疑。例如,《周礼·秋官·小司寇》载:“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于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注释说:“读书则用法,如今时读鞠已乃论之。”唐代经学家贾公彦疏曰:“云‘读书则用法’者,谓行刑之时,当读刑书罪状,则用法刑之。”这里所说的“书”,其实也就是判决书。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陈舜臣说:“‘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来的形状,‘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据此推断,殷代已经将正式记录写在竹简或木简上,这些记录兴许就包括判词。只可惜竹简或木简太容易腐烂了,没有流传下来。而保存下来的甲骨,主要记载的是卜辞之类的东西。比较早的一次诉讼,发生于周灭殷之前的西伯昌时代,传说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当看到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作了让步。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有狱”。
《国语·晋语》记载的一件讼事,倒还详尽,可以还原当时宣读判决的场景。说的是晋惠公六年,一位叫作庆郑的大夫,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擅自进退,失次犯令,且见死不救,以致晋惠公被敌俘虏。晋惠公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令执法官司马说将庆郑处以死刑。司马说在行刑前这样宣读判词:
夫韩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今郑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郑擅进退,而罪二也;女误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亲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郑也就刑!
在这篇判词中,不仅有对法律依据的援引,也有对本案事实的归入,诸般罪行,逐一罗列,用法刑之,无可辩驳。结尾的那句“郑也就刑”,且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但是,这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面判词,不过是对于宣读判决的记录。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判词文本,据称是西周晚期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篇 匜铭文。据说它记述的是一位叫作伯扬父的法官如何裁判牧牛提起的案件。铭曰:
惟三月既死魄甲申,王在棻上宫。伯扬父乃成劾曰:“牧牛, 乃苛勘。汝敢以乃师讼。汝上代先誓。今汝亦既又御誓,专 啬睦 ,周亦兹五夫。亦即御乃誓,汝亦既从辞从誓。式苛,我宜鞭汝千,幭 汝。今我赦汝,宜鞭汝千,黜 汝。今大赦汝,鞭汝五百,罚汝三百锊。”伯扬父乃又使牧牛誓曰:“自今余敢扰乃小大事,乃师或以汝告,则到,乃鞭千,幭 。”牧牛则誓。乃以告吏 吏曶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 用作旅盉。
这也是对一次诉讼活动的记录,不过却包含了较为完整的判词。有些生僻文字,虽然我也不十分懂,但大略能够体会到上古时代裁判的风采。当中对于牧牛一赦再赦,且辅以令其辞誓、以观后效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德主刑辅”思想在那个年代即成自觉。而在结构修辞方面,亦出手不凡,不仅案件事实与法律责任论列清晰,而且,第一人称的使用,也很有些“对话体”的意韵呢!想起清朝名吏樊增祥,亦喜用“汝”或“尔”直呼原告,未料竟在几千年前的上古铭文中寻到了根源。判决书首先是给当事人看的,所以,用第一人称进行直接对话,应当是最基本的形态,也最能发挥循循善诱的功能。只是,像 匜铭这样的判词,究属惊鸿一瞥,待到批量出现,已经相当晚了,按照明代学者徐师曾《文体明辨》里的说法,那已经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了。他是这样说的:
按字书云:“判,断也。”古者折狱以五声听讼,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吏为师,专尚刑法。汉承其后,虽儒吏并进,然断狱必贵引经,尚有近于先王议制及春秋诛意之微旨。其后乃有判词。
揣摩这话的意思,是说自打汉代实行“引经断狱”之后,才有了判词。所谓“引经断狱”,流行的称呼是“春秋决狱”,也称“春秋断狱”、“春秋决事”、“春秋决事比”等,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对此考据甚详,称其“是一书而二名也”。顾名思义,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中的经义和事例,拿来作为断案的依据。这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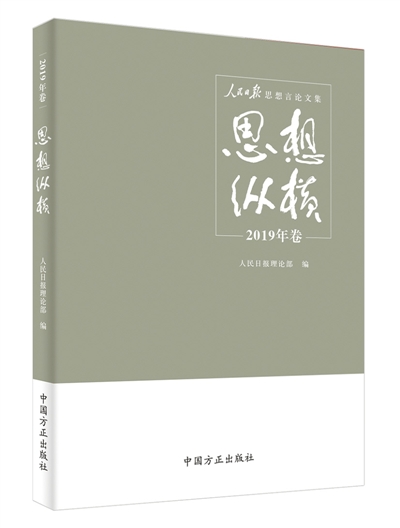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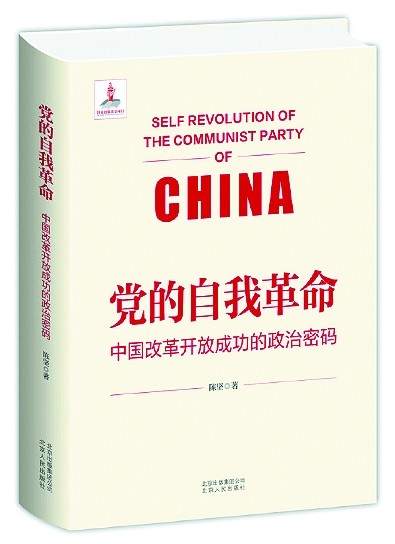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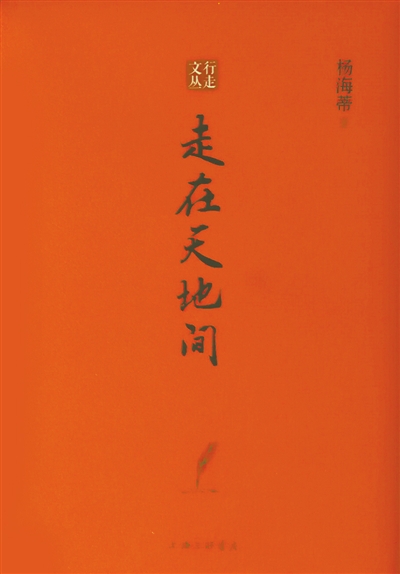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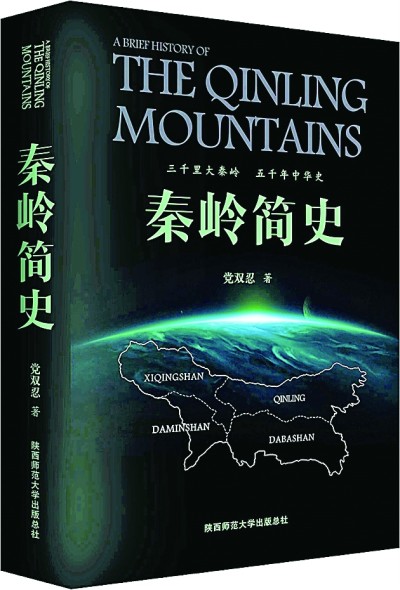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