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神州大地灾疫频繁,其中江淮一带,南北波及范围广、危害十分严重的大瘟疫有9次,徽州一府六邑无一幸免。数年大疫,“强村巨室,悉成莽苍”,民众对疫病的极度恐慌和无知更渲染了社会恐慌,“无知之民惑于渐染之说,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瘟疫可怕的传染性也使得“父子不相顾,兄弟不相往来”(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明清王朝腐朽官僚的怠办延误和救灾机制缺失,加剧了灾疫蔓延,以至于很多百姓并非死于疫情疾病,而是“汤药舒粥不继,多饥饿以死,乃归咎于疫”( 汪志伊《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饿殍盈野、哀鸿遍地的景象。
但徽州一府六邑并未像江淮其他地方发生“饥民抢掠四起”、兵燹不断的社会动荡,因为地方官府社会调控措施和民众救荒义捐的“义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瘟疫状况和特点
史载,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灾害次数频繁,达到289次之多。其中,水、旱灾害最为频繁,疫病灾害一共14次。旱涝灾后,“人物相感缠而为患”(汪志伊的《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灾后饥荒又使“盖饥寒之民离家就食,昼暴夜露;或遭风雨,必成疫疠”(《方苞集》下集外文卷五《与徐蝶园书》)。
《徽州府通志续编》这样记载:徽州地区“六邑饥,又大疫”“大饥,斗米一钱八分, 民大瘟疫,僵死载道”,甚至出现“孤村几无人烟”现象。大量灾民病亡及流离失所,耕田荒芜,造成粮价上涨。《徽州府志》记载“戊子己丑六邑饥,斗米一钱八分”,按明制,一石为十斗,即米一石需银一两八钱,比万历年间的平均米价每石六钱八分左右,增涨了164%。
万历十八年,面对灾荒饥荒不断,疫病流行严重状况,时任吏部员外郎的邹元标上疏万历皇帝:“今之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户部覆本中提议:“此后各省直有遇重大灾疫,许令各府州县,作速申文,合于抚按,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或买药饵拯救,死者或买棺木,或设义挥殡埋”(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可是,这些基本的救疫措施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才可实施。明中后期,朝廷自宋元时期设立的大疫救灾的惠民药局等功能作用逐渐减弱尽失,以至万历十年到十八年全国疫情暴发之际,朝廷竟无系统有效的救灾治疫办法。朝廷腐朽官僚的怠办延误,加剧疫情蔓延,引发社会动荡和盗情四起。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安抚民心,徽州一府六邑一方面发布告令,采取严厉的惩治措施,歙县知县彭好古为严厉打击盗贼发布教谕“迨至凶年而人人相戒曰:宁死饥,毋死盗也”( 万历《歙志》传卷一)。另一方面,府县官员和各村乡宗族组织积极开展教谕引导,并采取激励和调控措施,形式多样的民间救灾抗疫的“义治”兴盛,及时弥补了官府治疫救灾中缺银少粮的空白。
灾疫中徽州官民救灾治疫中“义治”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府和宗族组织除了在灾疫中发挥非常有效的社会调控功能外,还激励和支持商贾和乡贤乡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救灾治疫义捐活动。
(一)徽州官民救灾治疫中“义治”举措
推行聘医施药分丸。疫病暴发之际,由于明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的小规模的惠民药局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江淮南北地方官府为稳定社会往往将救灾治疫纳入官府职责范围,积极采取了延聘名医、制药分丸和鼓励民间“义治”的措施。在新安医学盛行的徽州,各地新安医家进村入户医诊施药。官府和宗族组织鼓励和组织医家开展形式多样的“义诊”活动,弥补了官府和宗族组织救灾治疫的不足,徽商们也积极解囊相济,形成当地广为赞誉的“义治”现象。明代医家张明徵,“世精岐黄,业授太医院官,后回籍开馆施药”,以至徽州村乡“四方踵至,应之不倦”( 民国《婺源县志》之《人物·义行》)。嘉靖年间,“祁门县内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哭声载道”,祁门县朴墅乡名医汪机“免费施治,救人不可胜记”。传曰汪机“久之求者益众,所应益博,活人至数万”(李汛著《石山居士汪机传》)。婺源县商贾程大防对“疾病不能致医者,为施方药,多所全活……邑侯重之,礼以宾筵”。清时期盐商汪应庚疫“在扬则施棺槥、给絮袄、设药局、济回禄、拯溺舟、育弃婴”“时疫疠继作,更备药饵,疗活无算”(《汪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
推广备荒仓储、激励义仓建设。一是普建预备仓。预备仓是明代朱元璋起始推行的备荒仓。弘治《徽州府志·恤政》记载,徽州府的预备仓数量充足,县府预备仓的数量大多在4所以上,而且逐年增加,休宁县曾增加到15所。仓储谷数充足,弘治前全府预备仓储谷数竟达到23万多石,平均每人拥有近半石的救灾粮,大疫中杜绝饿殍盈野现象发生。到了明中期后,预备仓颓废,管理混乱,储谷减少。《徽州府志》中写道:“粜及赈,大半饱积胥市猾。乡民赴领,忍饥待哺,至有不偿往返费,间持空囊以归”( 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二是兴建廉惠仓。《徽州府志·恤政》载:“正德十二年丁丑,知府张芹买田三千亩,令六邑作廉惠仓备荒。”在太守张芹的力推下,徽州六邑普建廉惠仓。《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也记载婺源县廉惠仓计“田二百六亩八分三厘一毫,岁收稻三百七十九石二升,系张公捐赎所置,贮仓备赈”。绩溪县廉惠仓“正德十二年知府张芹买寺田收租积贮备荒,嘉靖四十年人宏济仓,万历四年,知县陈嘉策重建”(嘉庆《绩溪县志》卷三《食货·积贮》)。可见,这种官办性质的备荒仓储起到了灾疫之际官府无法拿出平籴资金时确保赈灾粮供需的作用。而且,在官府岁银紧缺时,徽州一些富贾乡绅积极输粟官府,确保粮仓充盈。《沙溪集略》之《祥异》卷载:“乾隆十六年辛未夏秋冬三时,亢旱,赤地千里,民饥食寡,斗米五钱,知府何公达善、知县王公鸣劝谕捐赈减粜,里中批捐米石赈济族人。”到了明中后期,廉惠仓难逃被侵渔的厄运。《绩溪县志》这样记载:“廉惠、仁济二仓所收寺产银多被侵渔,民无实惠。”为填补官府赈灾粮食储备的空缺,徽州各村乡宗族组织积极介入备荒,组织乡绅族人筹资兴办义仓和社仓。
三是义仓与社仓兴起。义仓与社仓系民间资本籴谷备荒的仓储。徽州早期赈灾,主要是乡贤乡坤和商贾捐输祠堂祠田的籴谷,以此接济穷困潦倒的族人。明万历年间,在广德从商的歙县沙溪凌景芳,“尤喜施与周急赈穷”“乃捐其资置田与族饥馁者,共亩计之凡有若干;创屋与族无依者,共楹计之凡有若干。又置冢一区,与族之死无归者,共族之人养生丧死无憾。”(乾隆《沙溪集略》卷)歙县县令林元立由此赞叹不已,亲自作《凌氏义田记》写道:“凌景芳者,其义士欤!”
明中叶后,为弥补赈灾救疫空缺,徽州乡村普建社仓。万历《休宁县志》记载,万历九年,休宁县全县共有社仓37所。祁门县知县刘一爌在祁门县建社仓60所。婺源县也“四乡或置义田为仓”(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社仓建立之初,贮谷有官府倡募,但主要是民间集资。祁门县社仓官府“给本银四百七十一两,买稻一千五百七十石,并各约输稻,令乡约分贮各仓备荒”(道光《祁门县志》卷十四《恤政》)。社仓义谷发散和管理也是由民间义士承担,官府只是发挥组织领导的作用。
广泛募捐赈济饥民。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徽州府县积极筹备充足的赈灾粮款赈济饥民。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大疫之时,祁门县赈济稻谷3151石、银1420两,赈济灾民达12050人,杜绝了“道殣相望”“人相食”现象的发生。
在宗族组织的推动下,各邑贤达商贾广泛开展赈粥、赈粮捐银等赈济饥民的活动。歙邑灵山人方灌“佐彭侯(即彭好古)输粟以赈,而于里中又计口授粮,存活甚众”(道光《歙县志》卷八《人物志·义行》)。婺源县汪逢阳,“平粜施粥济饥,赖活无算”( 乾隆《婺源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义行一》)。民国《婺源县志·人物·义行》卷中记载了明代311位捐资捐粮“义行”的徽州贤达轶事,当地官府积极倡导和激励乡民踊跃义捐。明黟县县令在其《旌义堂记》赞誉了乡民胡彦本捐谷赈济善行:“正统辛酉之年,予宰黟县。岁旱饥,耆民胡彦本慨然出粟一千二十石赈乡人千四百三十户有奇。予以奏闻,上遣使赍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且复免其丁役”(嘉靖《黟县志》卷十四《艺文》)。正统九年至嘉靖年间,黟县当地因捐银捐谷善行义举受到朝廷和各官府敕赐建牌坊旌表其功德的“义民”达7人。
施棺建冢、掩骼埋胔。大疫之年,由于疫死之人“多疠气薰蒸所致也,一经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灾沴之祲也”(汪志伊《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所以,礼仪教化下的徽州,十分重视亡故宗亲的安置。除了官府设立义冢外,民间商贾乡绅更倾心致力于施棺建冢善举,“一听贫民无地者葬焉。无棺者给之”(弘治《徽州府志》卷五《恤政》)。婺源县城西人汪逢阳,“性慷慨,勇于行义”,万历十六、十七年,瘟疫暴发时,曾施棺埋葬三百余冢。
成化年间,歙县环溪商贾朱克绍在歙县二十七都汪村捐资买地设立义冢,且“复买地二亩收租以备每年清明日设馔祭之”。“成化十八年新安卫千户于明捐己赀买山地一十余亩,遇有贫难不能葬者,皆给棺葬之。有司为之立籍。” 明代歙县乡贤吴文光在万历饥荒大疫时,设“糜粥以饲饿者,出钱米以周贫乏,施棺槥以揜道殣”(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不仅如此,徽州乡贤还广建义宅为灾疫中四处流落、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之所。明弘治甲寅年间,歙县岩寺佘姓乡民建义宅“为屋若干楹”,专供那些灾疫之年颠簸漂流的灾民和族亲安身,“凡族之疏而屯者,听入居之”,颇受乡民赞颂。明徽州著名大学士程敏政为此专门撰写了《佘氏义宅记》赞道:“若论范之义庄,郑之义门,世可多见乎?况出于一廛之下,布衣之士能居其族而不使之沦没,可不谓义乎!”
通商平粜,拯救灾民。灾疫之年,官府和民间均采取通商平粜措施救灾,其中平粜粮价拯救饥民成为徽州民间参与“义治”救灾的特点之一。《沙溪集略》卷四记载了徽商凌顺雷灾疫之年冒着暑热奔波苏皖,购得谷米“平价以售”之轶事:“岁辛未旱饥,道殣相望,公虑市米无多,人有怀金钱而枵腹终日者,乃冒暑热往返江苏间采买接济,道经严陵青溪,居人阻截,公等筹画申理得直,故米艘得源源而来,平价以售,如是者数四,乡里赖之。”民国《婺源县志·人物·义行》也记载了程一庆的商人在“岁饥”之时,“减价平粜,远近至者日数万人”。
(二)徽州官民救灾治疫中“义治”特点
综观明清治疫中徽州官民“义治”现象,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参与人员众多,救疫的阶层广泛。灾疫中不仅有徽州府县申报领受灾银谷物赈济灾民、减赋缓征、劝谕地方宗族组织和乡贤商贾救疫行动,还有各宗族和乡贤商贾及族人兴起的捐银捐谷施粥供粟等义捐救疫活动。同时,官府鼓励富民平粜出粟,给予旌表,有力不出者予以惩罚。各邑乡贤绅商竭力配合官府和宗族积极救灾,普通庶民也倾囊而出,以救时疫。歙邑谢氏兄弟,家仅千金,却倾囊而出,以赋饥民。徽州商贾为救疫“输金千万而不惜”(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卷十五《尚义》)。正是徽州上下齐心协力、万众抗疫,万历十六年、十七年瘟疫流行时,徽州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无数百姓得以生存下来。
其二,多方施策、精准救疫。徽州旱涝灾害易发多发的环境使当地官府和民众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疫经验。嘉靖时佥事林希元总结救荒有六急“垂死贫民急饘粥,疾病贫民急医药,病起贫民急汤米,既死贫民急募瘗,遗弃小儿急收养,轻重系囚急宽恤”(汪志伊《荒政辑要》卷首《纲目·荒政丛言》),这些大疫中的六急措施在徽州均得以实施。由于徽州基本是旱涝灾后有大疫,饥饿灾民免疫力低,极易染上疫病。于是,徽州各界的祛疫自救中,以施粥供粟为首要措施,除了官府输粟外还组织乡里村民广泛开展施粥供粟以解抗疫中的燃眉之急。歙县岩镇人吴文光,“设糜粥以饲饿者,出钱米以周贫乏”现象不胜枚举。瘟疫暴发之际,义诊施药又成为控制疫情的必要手段。徽州新安医学明代已自成一体,涌现出了大量的医学世家,瘟疫暴发之时新安医家拯救人们于危难之中。休宁人余淳,精于医术,“值万历戊子岁大疫,出秘方全活不可胜计”(《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医部·医术名流列传》)。
其三,徽州宗族组织引领率众成为治疫的力量支撑。一是宗族组织教化引领作用。徽州宗族尤为重视道德礼义教化,徽州“自朱子后,多明义理之学”,徽州社会普遍有着知书达理、循规蹈矩、修德崇善的文化传承,由此养成了灾疫之际济贫救困、行德仗义的优良文化传统。二是推崇行善义捐活动。不仅建立完善的社仓义仓捐输管理制度,还广泛组织族人积极参与施粥捐粟救治饥民。激励和支持培育新安医药世家,聘请名医义诊,施药接济灾民,组织设立义冢收掩“以揜道殣”。
其四,儒家义利观和仁爱思想的道德教化成为灾疫“义治”思想文化渊源。在理学大师、徽州人朱熹仁爱思想和义利观的熏陶教化下,“儒风独茂”的徽州社会形成了帮贫济困的习俗。在徽州宗族看来,大灾大疫中,赈灾施善、解救灾民无论是官府贤达还是庶民都是应推崇赞颂的德行善举,对于彰显“族党之望”“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所以,在这种行善义举文化习俗中,徽州商贾乡贤儒士都热衷于义捐义赈,即使是赤贫之士,也节食省餐,依然急公趋义“黾勉积蓄十数年间而一旦倾橐为之”(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五《尚义》)。清乾隆年间,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两淮盐法道员鲍启运两兄弟“置体源户田五百四十亩,专以赡给族间四穷(鳏、寡、孤、独),归诸宗祠”,鲍启运为灾疫中还有“贫乏者,每届青黄不接之际,众口嗷嗷”,于是,“亟又置敦本户田五百余亩”。由此可见,明清治疫中徽州官民“义治”善举有着其道德思想根基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对于当下的抗疫或许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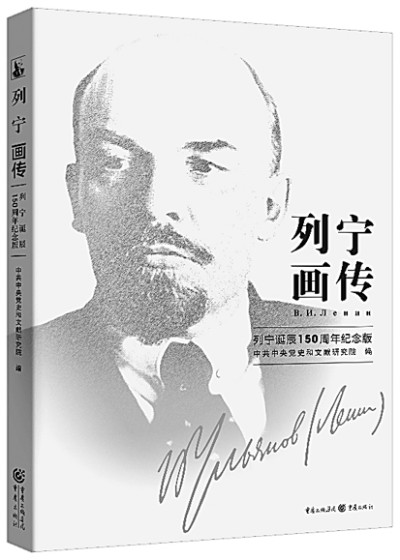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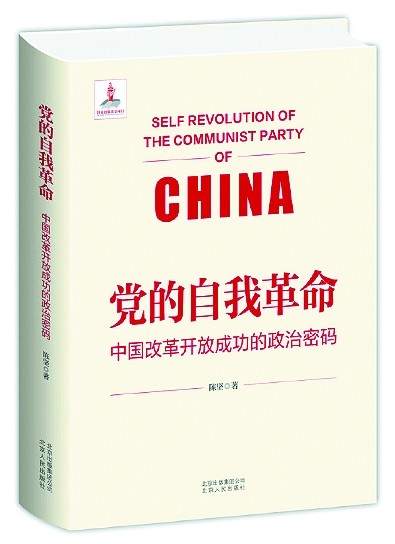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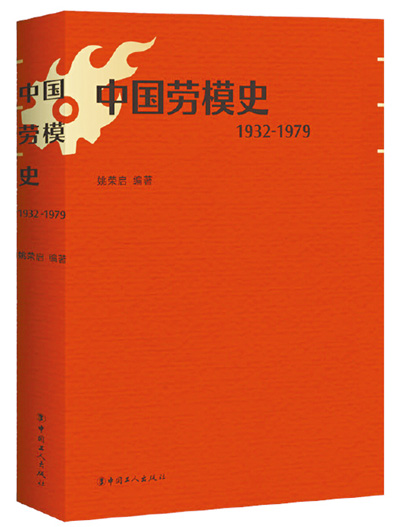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