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国际商事调解在国际法治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和国内商业事务的纠纷解决越来越多地使用调解代替诉讼的背景下,2019年8月7日,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历时四年研究拟订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向各国开放签署。因其签署地在新加坡,因此也称《新加坡调解公约》。
中国作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成员国,全程参与公约的制定,当然也作为首批签约方签署加入。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代表了我国对多边主义的认同,也为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和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国执行提供了新的进路。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第六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联合国文件A/CN.9/861)中提到,工作组决定在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上,参照《纽约公约》的做法采用直接执行机制,也即国际和解协议如同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一样,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具体表现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每一当事方应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并根据本公约规定的条件执行和解协议。”因此,如何对来我国申请执行的国际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是在《新加坡调解公约》落地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执行审查制度的定位
依据现行法,国内非诉调解协议并无执行力和既判力,需要司法确认程序赋予其效力方可执行,于此便与国际和解协议的直接执行机制产生了矛盾。然而,此矛盾并非无解。
虽然《新加坡调解公约》确定了直接执行机制,但是,并不等于对任何国际和解协议都要径行执行。工作组表示,即便对国际和解协议采用直接执行机制,但是并不代表缔约国对其没有审查的权力。《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第4条和第5条就分别规定了国际和解协议要在缔约国执行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只有满足公约规定条件的国际和解协议才能被执行,而判断其是否满足条件,则必须经过执行前的审查程序。
执行审查制度的作用是判断国际和解协议是否符合可执行的条件。在未来的程序构建上,可以对国际和解协议和国内非诉调解协议区分对待,以司法确认程序赋予国内非诉调解协议以执行力,以执行审查程序确认国际和解协议是否可以执行。二者是两种并行不悖的执行程序,而二者的区别除了针对的对象有区别外,在程序的设计上,审查的内容、审查的结果以及被驳回申请后的救济都应当有所区别。
执行审查的范围
《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审查范围
主动审查范围
当事人向缔约国申请执行时,缔约国主管机关可以主动审查的内容规定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第4条以及第5条第2款。其中第4条规定的是关于国际和解协议本身应具备的形式要件,主要是各方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以及证明其产生于调解的证据。公约条文对证据形式进行了清单式的列举,包括调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的签名、调解员签署的表明进行了调解的文件、调解过程管理机构的证明,只有上述证据无法举出,才允许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而第5条第2款规定的主要是关于国际和解协议内容实质上是否违反执行地公共政策、争议事项根据执行地法律是否可以以调解方式解决。
被动审查范围
《新加坡调解公约》第5条规定了被执行人向缔约国主管机关申请拒绝准予救济时所要提出的证明,对于这些事项,主管机关不能主动审查,仅在当事人提出抗辩以及证据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审查。范围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解协议的真实有效、有明确的可履行的内容以及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是否公平中立和遵从职业规范。
我国对执行审查范围的构建思路
对主动审查范围进行细化
主动审查的范围是申请执行的国际和解协议应当满足的基本要求。对于《新加坡调解公约》所列举的事项,我国应当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其原因在于:
首先,细化主动审查范围,将其尽可能的明确化、具体化,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审查法院对当事人自愿处分的干预。
其次,为适应各国不同情况,国际公约的规定本不就宜事无巨细,很多规则并未显示于文本。如第4条中并未将“受到胁迫”和“欺诈”明文规定为抗辩理由,并非因为受到欺诈与胁迫的国际和解协议仍可被执行,而是因为它们属于公约条文的应有之义。我国在《新加坡调解公约》落地过程中,应当将对于国际和解协议的原则性的要求落实于纸面,以便更好地施行。
申言之,在形式审查方面,《新加坡调解公约》对于何种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调解准则,何种情形属于调解员,以及如何判断是否由违规行为导致和解协议的订立,并没有作出具体解释,仍有待于在落地过程中参考域外经验,以及在国内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以上情形予以细化。
而在实质审查方面,法院对于内容违反“公共政策”的国际和解协议可以拒绝执行。然而,问题在于,何为“公共政策”?以《纽约公约》的实行经验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国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的态度是,违反国内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仲裁裁决,并不一定构成对“公共政策”的违反。
由此可见,在我国后续的商事调解立法过程中,法院可因和解协议违反“公共政策”而拒绝执行的范围,更不能够按照民事合同的无效情形来确定。因此也应该对于“公共政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明确的细化,避免法院以“公共政策”为由过多限制和解协议的执行。
对被动审查范围进行扩张
商事调解本应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意愿,法院不宜过多干涉。但是,当事人一旦对于和解协议的执行提出抗辩,就说明当事人对于协议的“自愿性”提出了质疑,希望法院介入并予以审查。
这种抗辩赋予了法院对于协议进行深入审查的正当性。
所谓被动审查范围,其实是作为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救济。由于国际和解协议是具有执行力的文书且极大可能并非在我国订立,因此笔者认为,在衔接公约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对于被执行人以及案外人的权益进行保护。公约落地时可以结合我国执行程序中的救济制度和国际和解协议的“国际性”与商事调解的特殊性适当扩张救济尺度。
执行审查结果
对于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审查结果,可以参考我国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我国目前对国内和国际仲裁裁决是区别对待的。对于国内仲裁裁决,法院既可以因为仲裁的不合法而撤销,也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裁定不予执行。而对于国际仲裁裁决,法院只能作出不予承认或者不予执行的裁定。
由于国际和解协议与仲裁裁决一样具有执行力,且依据《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定,缔约国在执行国际和解协议时,是不允许设置前置承认程序的。这样的规定本意是为了保证国际和解协议不会因某一国的不予确认而丧失执行力。因此,我国在构建执行审查制度的过程中也应当注意,法院对国际和解协议只能够作出“准予执行”或者“不予执行”的裁定,而无权对其撤销。
结语
在商事调解的历史上,《新加坡调解公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决定。如何尽可能充分发挥公约的积极作用,减少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冲击,是我国商事调解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命题,执行审查制度的构建只是其中一步。我国应以加入公约为契机,推进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商事调解制度,为推进国际贸易往来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助力。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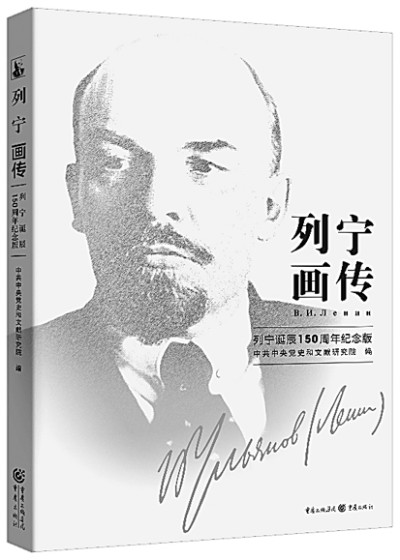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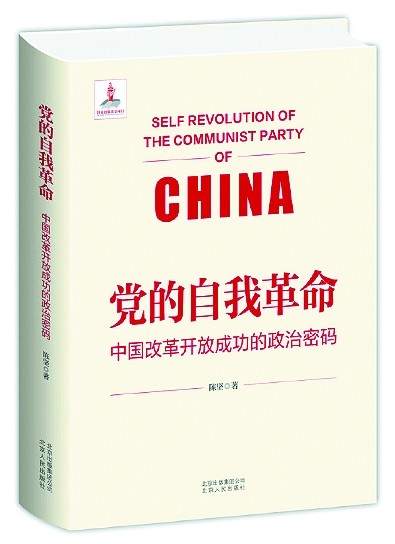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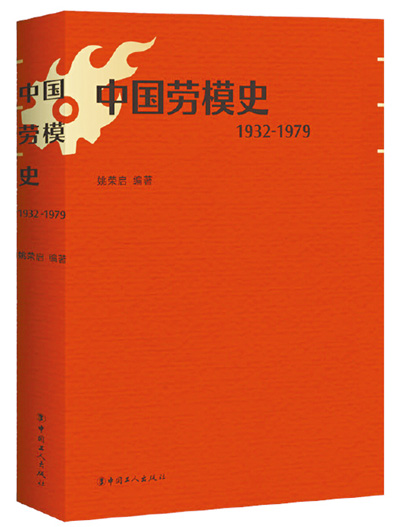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