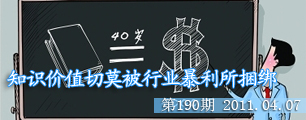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我与《马兰花开》剧组结缘是在2011年12月22日,那个时候这部戏还不叫《马兰花开》而是《邓稼先》。因排练和演出所点亮的近700天的“老邓”生活,是戏剧之神给予我的慷慨馈赠。这段日子,我始终浸润在他的世界里,从陌生到熟悉,从茫然到促膝,我分明感受到,在摸索中一步步向他靠近。
“出演邓稼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回答了不知道多少次这个问题,但答案却没有一次能够令我满意。因为最真实的感受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它更像是一个人独身于漆黑的荒原,偶遇一盏微弱的萤火,循光而行,蓦然抬头间,却看见了崭新的世界。
“邓稼先”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他与新中国的崛起紧密相连。但如果追问对他的认识,那么除去原子弹和氢弹之外,却几乎所剩无几了。这便是我翻开第一版剧本前的状态。当时我以为,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邓稼先,一位科学巨匠,必是执着和睿智的“神”。可是,第一次朗读剧本的时候,我手脚冰凉、头皮发麻,好几次都落泪了。我没想到,他来自如此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他经历了那样颠沛流离的童年,当时的研究环境竟恶劣到了那样的地步,他有一位一生的挚友,叫杨振宁。更没有想到,为了新中国的核事业,他可以牺牲至如此地步而不自知,直到牺牲自己。
我开始不理解他了。他的父亲邓以蛰先生是著名的美学教授,他的夫人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先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自己是留美归国的物理学博士,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一条路?若想不通这些过往,我的每句台词都将成为空谈、成为失去灵魂的干瘪句子。而我也意识到,不能用后续一系列的成功去概括邓稼先选择的人生之路。因为在他决定隐姓埋名的那个时刻,他怎么可能知道在未来28年的生命中,到底会发生什么?成功了固然可喜,那如果失败呢?还值得吗?带着这些费解,我必须去触摸他当时做出选择时的心境,这种选择本身,甚至比成功更加弥足珍贵。
去年3月,剧组一行数人去绵阳探访邓稼先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即“九院”。邓稼先担任九院院长时,院址还设在深山里,我们一路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向大山深处进发。车子走了很久,当我们看到窗外一间红砖砌成的小平房时,当年给“老邓”开过车的一位老师傅说:“到了到了,这就是老邓的小院。”当时我的心跳得特别快,因为第一次觉得离他那么近。小平房里的陈设实在太过简陋,灰暗而且有些压抑。打扫卫生的阿姨说因为这里很偏远,来的人很少,这些年基本就没动过。我突然想,在这样的环境里,老邓想起在美国时先进的仪器设备,想起在北京的家人、亲友,他是怎样的心境?
第二天下午,我们拜访了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我们来到花园路一处平常,甚至有些老旧的小区,在一幢明显经过了数十年风吹雨打的家属楼前停了下来。我没想过,一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的妻子、一位前国家领导人的女儿,在耄耋之年,竟独自生活在这里?更大的震撼发生在我进屋之后——屋内的陈设还保持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原貌,“邓稼先的屋子我完全按照原样给保留了下来”,她说。那天下午,我们静静地听许老师讲了很多,她讲得很慢、很轻,好像往事并没有走远。也就是从许老师的描述中,我们毫无阻隔地感受到了那个喜欢交响乐、爱看戏、爱下棋也有时充满孩子气的邓稼先。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质朴科学家。
无论文献、纪录片还是邓稼先亲友、同事的描述,有一个形容词总会出现,那便是“纯粹”两字。邓稼先实在是个纯粹的人,面对工作,他的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能把工作做好,所以九院上上下下,从学术大师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对他敬重有加。面对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他把用工资买来的点心、糖果分给每一位同事,同事们最喜欢到他的宿舍开会,因为这意味着又可以趁机“补充营养”。“纯粹”赋予了邓稼先高尚的人格,也赋予了他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对人对事,不含杂念——这就是他足以在科研和管理上均站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领袖位置上。
今年8月,《马兰花开》剧组一行开始第三季的巡演之旅,第一站即是新中国最早的核武器试验基地所在地——青海。穿过罗布泊边缘时,大漠的荒凉使得本来嬉闹的车厢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相信在我们脑海中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当时老邓他们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核武器的试验的?”
在基地,我问一位入伍7年的班长:“家里人知道你在哪儿当兵吗?”他憨憨地笑了笑:“只知道我在祖国的西部当兵,不知道在哪儿。其实我哥哥在这边做生意,离我也就3个小时的路,但我不能说,我俩7年没见了。”当真的面对他们时,我才知道那些“不知道、不能说”之中,蕴藏了对亲人多少只能深埋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