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打破旧藩篱、开辟新格局的气度
先生一生的重要学术贡献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众所周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珠玉在前,后继者如何突破前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限于宋元时期,从史前时期写起,最后以民国时期的话剧结尾,这是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在构思框架上的自家设定,于此,开辟新格局的气度显而易见。
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戏曲学界的叶德均先生曾说:“近人治戏曲而有所成就者,首推王国维,其次便是吴梅。王氏所著《宋元戏曲史》《曲录》等不仅考证精确,而且奠定了戏曲史研究的基础。……至于吴梅,据说是‘不屑于考据’的,而其成就是在作曲、度曲、制谱、订谱的诸方面。”当时,王、吴二家,如果说不上旗鼓相当,也可算是双峰对峙了。正如叶德均所言,吴梅长于治曲,其主要著作《顾曲麈谈》全书离不开一个“曲”字;其《中国戏曲概论》即以“乐府亡而词兴,词亡而曲作”一句开头,书中将元明清的剧曲与散曲相提并论,虽边界不清,却也能够粗陈梗概。至于王国维,其视野稍有不同,既着眼于宋代大曲、古剧脚色,也触及“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其《宋元戏曲史》更是对宋元时期的剧本文学情有独钟,其中的元剧之文章、元南戏之文章等脍炙人口。可以说,王、吴二家各有特色,于戏曲学均有开创之功。
相较而言,每戡先生的自家设定可谓突破前人,胆气与学识兼备。
先生不同于王、吴二家的是,跳出曲学的旧藩篱,将文本与剧场联系起来考察,不仅看到曲,更是重视剧。因而,书名不叫《中国戏曲简史》,而称《中国戏剧简史》,一字之别,大有深意。
先生在本书的前言里曾经夫子自道:“过去一般谈中国戏剧的人,几乎把戏剧史和词曲史缠在一起了,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即贤明如王氏(国维),也间或不免,所以他独看重元剧。我以为谈剧史的人,似不应该这样偏。”这就流露出其著书的基本思路:将戏剧史与词曲史“切割”开来,重新审视戏剧的特性:“戏剧本来就具备两重性,它既具有文学性,更具有演剧性,不能独夸这一面而抹杀那一面。评价戏剧应两面兼重,万一不可能,不得不舍弃一方时,在剧史家,与其重视其文学性,不如重视其演剧性,这是戏剧家的本分,也就是剧史家与词曲家不相同的一点。”不可忽视其自家身份的重新确认,先生不做词曲家,而自觉地担负起剧史家的重任,这是中国戏剧史研究的一条分水岭。
先生从东西方戏剧的最大通约性出发,指出中国古代戏曲的价值主要在于剧。当然,不同民族的戏剧,除了相互间的通约性之外,还有各自不可通约的民族特性。就民族特性而言,所谓戏曲,前人重视曲不无道理;可戏曲明显地不仅仅只有曲,先生有意识地要摆脱长期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曲学误区”,与众不同地强调了戏曲中的舞,并由舞及戏,去探索中国古代的剧史的生成与演变。他更重视戏曲中动态的东西即动作性,他要探讨戏曲的民族特性背后的内在因素。
先生曾从民俗学、语源学等方面审视中国戏剧形态的发生、演变诸问题,提出了“戏由舞来”的基本看法。他说:“戏由舞来,舞者就是后世的演员,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戏,几乎都是由古舞演变进化而来。”他又说:“戏剧固然需要歌曲或者语言(宾白),倘使没有,戏剧还是戏剧,‘默剧’不就是原始的戏剧吗?”当然,就戏剧史研究这一学科而言,先生的“戏由舞来”的结论,还可以作更深入的讨论,但与别人相比,其研究路子显然是更注重中国“戏曲”的动作性,更贴近戏曲作为综合性舞台艺术的特质。
故而,先生的《中国戏剧简史》即以“戏由舞来”作为全书的逻辑起点。此书自成格局,贯通古今。全书分七章,即:考原(史前时期),巫舞(先秦时期),百戏(汉魏六朝时期),杂剧(唐宋时期),剧曲(元明时期),花部(满清时期),话剧(民国时期)。先生综合考察了中国戏剧从巫舞到戏曲、再到话剧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生根据戏剧的本质,开创性地把戏曲与话剧两个领域打通,体现出十分可贵的探索精神。同时,他注重研究戏剧在不同时期各自的形态,注重观察唱、做、念、打诸因素不断演化的轨迹。他认为,随着时代、社会的进步,旧的戏剧形态会被新的戏剧形态所扬弃,而旧戏中有生命的东西,也会在新戏中延续下来。所以,在《中国戏剧简史》的最后一章,先生对民国时期的话剧有如下看法:“这一期,我认为是中国戏剧的新生期。”写作这一章,先生以与时俱进的治学态度观察和研究这个“中国戏剧的新生期”之所以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并以一种颇为自信的语调结束全书:“历史的轮子不会倒退,民主的时代潮流也无法抗拒,光明爽朗的前途终会走到的。”如此写作戏剧简史,可谓一家之言。
2.本土之外的学术视野有助于本土化认知
先生与王国维有一个相似点,即都具有本土之外的学术视野,这与他们都曾经走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或做研究有很大关系。可是,就戏剧研究而言,先生却写出了一部王国维没有写过的《西洋戏剧简史》,这似乎是一个异数,但在董每戡的学术生涯中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读各种董著,经常会看到他对外国理论的引用、跟世界名著的对比,其本土之外的学术视野早已内化为他的阅读经验和知识储备,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会适时地关联起来,或者是确认文学世界之“同”,或者是分辨本土之外和本土之内的相异之处,从而加深自己的本土化认知。
先生对于本土之外的学术和文艺作品是下过功夫的,并非浮光掠影,且以《西洋戏剧简史》为例,并以之与当今流行的同类国外著作略作对比,可证并非虚誉。
《西洋戏剧简史》的全书框架分为三个时期:古代期、过渡期和近代期三部分;所谓“西洋”,实际上涵盖欧美多国。此与欧美学者所写的通行的世界戏剧史著作大致相符。比如,美国学者编写的《世界戏剧史》,开头部分有三章:戏剧的起源,古希腊剧场与戏剧,希腊化时期、罗马、拜占庭的戏剧;第四章就是“中世纪欧洲戏剧”。而《西洋戏剧简史》的上篇是“古代期戏剧”,讲的是希腊、罗马,与《世界戏剧史》前三章大体对应;中篇“过渡期戏剧”,讲的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戏剧,与《世界戏剧史》第四章所述范围也大体相近。至于下篇“近代期戏剧”,从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等国一直讲到美利坚。相较而言,作为大部头的《世界戏剧史》,与《西洋戏剧简史》相比,自然显得更为丰富、细致,但无论如何,作为并非以西洋文学研究为主业的董每戡先生能够如此扼要地驾驭西洋戏剧史,起码不算外行。
何止不算外行,先生的具体表述和论析还颇有见地。我们不妨将先生介绍雨果的一段文字与上述《世界戏剧史》相关的文字对比看看,从中可以窥探《西洋戏剧简史》的学术含量:
(介绍雨果生平)……这里仅说他在戏剧上的成就。1827年举起浪漫主义的火把,他的《克伦威尔》一剧出世,这是他想以之证明自己的理论的东西。他认为不需要“三一致律”,重要的是动作,传统悲剧中的对仗、有韵诗都应摒弃,诗的作风必须自然,主张离奇,必须和恐怖合作一起;不过这剧还不是极好的作品。到了1830年,拿出杰作五幕十六场的《欧那尼》,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恶战便开始了。
这是先生对雨果前后两部浪漫主义剧作的简要评论。接着再读《世界戏剧史》:
法国的浪漫主义的理论宣言仍首推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1827)。维克多·雨果(1802—1885)呼吁抛弃时间和地点一致律,谴责文类上的严格区分,主张将戏剧行动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当雨果的《欧那尼》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时候,剧场内浪漫主义者与传统维护者之间的激战将演员的声音都淹没了,这种局面持续了几个晚上。
这部《世界戏剧史》初版于1968年(晚于董每戡《西洋戏剧简史》几近20年),到2008年已经出版至第十版,是风行全球的戏剧史权威读本。两相比较,同样的论述对象,就基本的信息来看,《西洋戏剧简史》没有遗漏;而就论述文字而言,先生相当精炼地点出雨果的戏剧观是“他认为不需要‘三一致律’,重要的是动作,传统悲剧中的对仗、有韵诗都应摒弃”;而《世界戏剧简史》说:“雨果呼吁抛弃时间和地点一致律,谴责文类上的严格区分,主张将戏剧行动置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二者的“学术含量”大致相当,表述却各有特色。
早在1939年,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序〈戏剧演出教程〉》,文中提到自己熟读西方戏剧史家马修的著作:“马修氏就是我一向敬佩的人,不要说别的,仅他的一册《欧洲演剧发展史》,便使我读而又读地读了三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生能够写出一部《西洋戏剧简史》的缘由。
事实上,读懂董每戡,像《西洋戏剧简史》这样的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先生的其他著作每每含有本土之外和本土之内的对比,《西洋戏剧简史》可以帮助进一步了解先生学术视野本土内外的复合性。如其《笠翁曲话拔萃论释》一书,研究的虽然是清李渔的戏剧理论,可在书中多次引用别林斯基、高尔基等的戏剧观点以作比较,有时甚至会说“这里可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补足李笠翁所未谈的”。此外,像《三国演义试论》一书,研究的是家喻户晓的一部中国小说,可先生会说,此书是“置诸14世纪的世界文坛、艺术画廊而毫无愧色的作品”,“我不能不忆起14世纪上半期世界文学艺术范围内的情况。据我所知,作家们理解精雕细琢人物内在和外在面貌的实在很少,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居然在这方面已经达到难得的程度了,这就足以使我们振兴民族自豪感”。原来,先生的学术视野的本土内外的复合性,其最终的落脚点正是本土化自觉。
3.本土化自觉与学术创新
如前所述,先生一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是中国戏剧史研究,可他跟一般学院派教授不同,他还是戏剧界的行家里手,不是一个关在书斋里的教书匠;他会编剧,懂导演,熟悉舞台,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活跃于抗敌演剧的前线,积累了丰富的“场上”经验,其长年的舞台生活决定着他在本土化自觉的同时从事于有异于学院派教授的学术创新。比如,他在重视戏剧的文学性的同时更为关注演剧性,这一点,他的学术贡献是超越了王国维和吴梅等戏曲学大家的。
先生强调演剧性,除了自身的实践外,还有影响着其演剧理论的本土话语。他相当推崇同样会编剧、懂导演、熟悉“场上”的清代戏剧家李渔,后者的名著《笠翁曲话》深得先生的重视,尤其是此书里的“演习部”,先生认为特别珍贵:“原因是历来的一切曲论家们无能谈,故不曾有人谈;而笠翁有编剧和导演的实践经验,才敢于谈。”在过去“剧学即曲学”的误区里,不容易在一群曲论家里找到知音,而李渔是先生认为难得的真正的行家。所以,李渔在《笠翁曲话》里呈现出来的演剧观,是先生演剧理论之本土话语的重要来源,也是其本土化自觉的具体呈现。
先生尤其赏识李渔“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八个字,当然,他对“专为登场”的内涵是有辩证把握的(其中含有对“本土之外”戏剧观点的借鉴和吸收),不会过度而片面地强调为登场而登场。他指出:“戏剧本来是具有‘两重性’的,它必须既具备着适宜于舞台上演出的‘演剧性’(或称剧场性,舞台的品性),又该具备着‘文学性’。……‘文学性’不仅指剧本的结构和词采,首先包括了那作为文学艺术之第一性的思想内容,光具有丰富的‘演剧性’而没有好的思想内容、结构和词采的剧本,事实上不能称之为一个好剧本,它至多只能够一时吸引观众,经不起体味。”辩证地看待“演剧性”和“文学性”的关系,是先生从事戏剧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独到之处,这跟他对世界戏剧史的考察、对作为中外戏剧的最大公约数的“戏剧性”的体认分不开。
从1958年冬天至1959年秋天,先生曾经写出一部60万言的《中国戏剧发展史》,不幸得很,书稿后来遗失不存。1979年5月之后,离开居住了21年的长沙回到广州,先生的最后岁月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转眼间就进入了1980年,迎接新春,先生怀抱着兴奋,他在1980年1月4日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因廿多年不露面,也得奋斗一年才行——(19)80年就是奋斗年。”先生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要知道,他在现实人生中已是“苍老衰翁”,“他曾有过长达半年没有迈出家门的记录,盖因气喘使他一动不能动,一动就喘上半天……因为肺气肿使他喉音嘶哑,气喘不已,讲话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对这种实际稍一失衡即可夺命的症候向未视作危险的杀手,他一直乐观地认为自己还能活五至十年。”(陆键东《历史的忧伤:董每戡的最后二十四年》)设身处地想一下,先生当时的兴奋,真有一种悲壮色彩;十分遗憾,没过多久,因为一次医疗事故,先生于1980年2月13日在广州辞世。他本来以为1980年就是他回到中山大学之后的“奋斗年”,每念及此,叫人唏嘘,也令人感佩!
(作者:董上德,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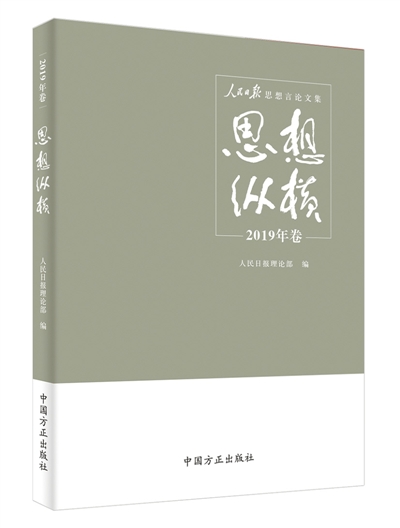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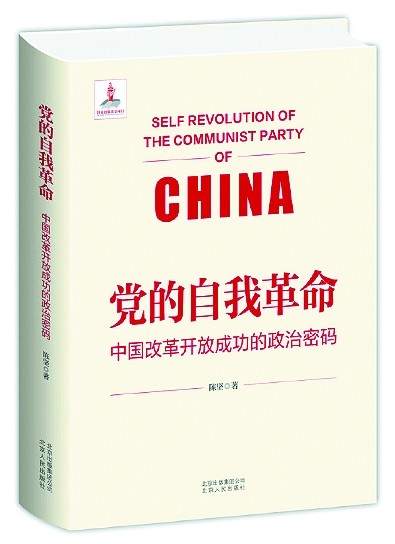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