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尊孔抑孟
大江健三郎认为,在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之下,孔子与孟子学说在日本社会受容与传承的际遇迥然相异——“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有利于天皇制,因而比较欢迎《论语》,同时认为孟子学说中含有反天皇制的因素,便对孟子及其学说持反对态度。”
观照孔孟学说东传日本的历史,孔子学说在圣德太子时期便奠定了儒家正统的地位,演变为天皇制伦理的法理基础,而孟子学说,则由于民贵君轻的基本政治伦理天然违背了天皇制自上而下的尊卑观,从而成为东传日本之儒教的异端。这种尊孔抑孟的主流意识形态,直至伊藤仁斋的出现,才得到反思和受到批判。
《论语》早在三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传往日本,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由于阿直歧的推荐,率治工、酿酒人、吴服师赴日,并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就是汉文字流入日本之始。其后继体天皇时(513—516)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高丽五经博士高安茂、南梁人司马达赴日,又钦明天皇时(554)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等赴日,这可以说是以儒教为中心之学术文化流入日本之始”。(朱谦之著《日本的朱子学》)
如果说这大约三百年间的儒学传入是时断时续的涓涓细流的话,那么到了七世纪,即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这涓涓细流就成了奔腾于日本本土文化这个河床中的汹涌洪流,广泛而持久地滋润着干涸的本土文化。在这个时期,有史可考的日本第一位女天皇炊屋姬,也就是推古天皇,为了抗衡把持朝政的权臣苏我马子,故而册封自己的侄儿、已故用明天皇的儿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便是后世盛传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对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则不断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借以如饥似渴地吸收和消化来自中国的先进文化,其中就包括从中国大量引入的儒学和佛教文化。圣德太子更是学以致用,很快便基于儒佛文化亲自拟就并于604年颁布了旨在对官吏进行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该《宪法》除去第二条之“笃信三宝”和第十条之“绝忿弃嗔”取自佛教经典外,其余各条尽皆出自儒学经典和子史典籍。
可以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论语》和《五经》都对《十七条宪法》带来巨大影响,从而为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做了前期准备。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部宪法引入《论语》者有四,而引入《孟子》者则为一。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引入中国儒学的初期阶段,或许是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不甚了解,圣德太子还是对孟子表示出了敬意,尽管在《宪法》中的参考和引用大大少于孔子的《论语》。
圣德太子去世后,孝德天皇在大化二年(646)颁布《改新之诏》,史称大化改新,提出“公民公地”,将皇族和大贵族的土地收归天皇所有,“确立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及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儒学的天命观及与之相联的符瑞思想成为革新的重要理论基点”,由此正式成立中央集权国家,并将大和之国名更改为日本国。随着神话传说故事《古事记》和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的问世,日本历代天皇越发强调皇权天授、万世一系,及至明治维新后,更是借助日本传统中对天皇的尊崇,以法律形式确认天皇被赋予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之地位,集统治权、军权和神权于一身。
于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主权在民、人民福祉才是政治活动之最大目的等孟子的政治主张,便不可避免地与日本历代统治阶层的利益发生了猛烈碰撞。于是,在孔子自被奈良朝奉为“文宣王”并享有王者至尊的一千余年间,孟子非但不能享受亚圣的荣光,就连其著述《孟子》也不得输入日本,致使坊间四处流传,不可将《孟子》由唐土带回日本,否则将会在回航途中遭遇海难……
这种尊孔抑孟的现象到了幕府时代也没有任何改变。进入幕府时代之后,“作为军事独裁政权的幕府政权一直提倡武士道及尚武精神,而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武士道形成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利用儒学阐释武士道,汲取了儒学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依其统治利益所需改造儒学,冀以充实武士道”。(刘宗贤、蔡德贵著《当代东方儒学》)
尤其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幕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牢牢掌控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绝对权力,转而废弃此前的儒佛并尊之国策,开始独尊儒家并将儒学尊为官学,同时废止除此之外的一切“异学”,把提倡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视为主导思想,并将其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幕府根据其统治利益所需而任意“改造”儒学,用以“充实武士道”,二是被幕府选中的、可供其“改造”的儒学或曰官学,便是“把纲常伦理绝对化的程朱理学”。由此可见,经过种种“改造”的这种所谓儒学,就只能是遭到严重篡改的“儒学”,为统治阶层的伦理纲常保驾护航的“儒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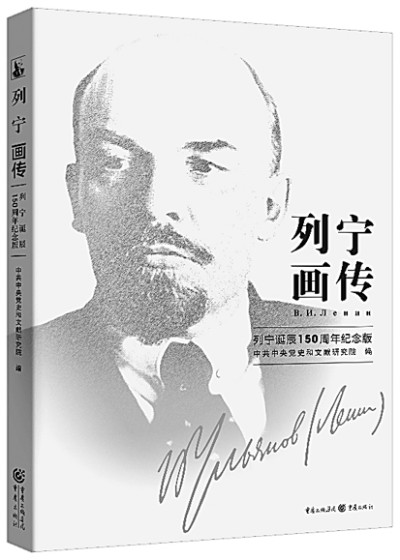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