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实绩,却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需要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军旅文学的每一次繁荣发展都是一次自身觉悟觉醒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时代发展主潮,探索重建当代军人精神世界,始终坚持军旅文学发展特殊规律,铸就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中国军人精神风貌的美学风范,为强军历史使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进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先声。
纵观中国历史,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美,诸如庄周的旷达飘逸之美,魏晋的风流洒脱之美,两汉的正大堂皇之美,盛唐的雄强庄严之美,两宋的文雅精致之美,并且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美学内蕴。这些美学风格的形成,无不与那个时代的历史境遇有密切的关系,好比种子,在不同的土壤环境里才会开出形态各异的花朵。
作为中国文学大河一脉的军旅文学,在将自身融入中国文学发展主潮的同时,也始终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美学特征,这源于军旅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特殊性。当我们悉心研读从《诗经》中的战争诗一直到唐宋边塞诗词等为数众多的历代军旅诗文,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判断,中国古代直至近现代以来的军旅文学美学风格始终传承着一个主脉,他们或悲壮激越,或慷慨豪迈;或沉郁雄浑,或气吞万里;或刚劲苍凉,或天马行空。正是由于其独特鲜明的美学风格,使得军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也或从一侧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民族文脉。
一代伟人毛泽东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仅见的一位深谙文学艺术及一切文化形态对民族革命及武装斗争巨大影响,并形成系统理论体系,而且还身体力行、笔耕不辍,终成一代“正事写史、余事写诗”,诗史合一的诗文大家。他于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党和军队的文艺属性的重新认识,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命题。此后,部队文艺工作也相应地提出了“为战斗力服务”的要求。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两支大军”(战斗大军和文艺大军)、“两个总司令”(朱总司令、鲁总司令)、“精神原子弹”等说法,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讲话》精神。
真正代表历史进步潮流的文学艺术所释放的无穷能量,堪比装备精良的百万军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日理万机,他都文思瑰丽,气象宏大,给时代和后人留下一批与中国革命相映生辉的宏文伟词。特别是毛泽东诗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唱,不少篇章已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以其豪迈大气、想象浪漫、文采华美的鲜明美学风格傲立于中华诗词之林。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与那个时代历史潮流奔涌前进的整体风貌相一致,集中代表了其中的精神底蕴,终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厚重一笔。
中国的军旅文学美学从来就不是凭空造出的,它根植于中国的历史现实境遇,代表了人们的普遍愿望,代表了时代的热切呼唤,代表了国家的富强梦想。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悄然火爆,点燃了人们血脉基因中对崇高理想的向往,随之《亮剑》《突出重围》《士兵突击》《历史的天空》等一大批弘扬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黄钟大吕之音,轰鸣如雷,强势回归,成为中国走向21世纪伟大征程的精神先导。
如果说,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是军旅文学的风范,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个传统,而不是弱化这个传统。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要求方面讲,如果中国军人放弃了对国家民族整体命运的担当,放弃了对崇高精神价值的坚守与重建,放弃了对正义战争的追问而堕入虚无主义,放弃了牺牲精神而迷失于个体物欲,那就意味着自身的消亡,意味着军旅文学的消亡。
军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守卫者,军旅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守望者,面对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我们要问的正是:中国军人何为?军旅作家何为?军旅文学何为?
军旅文学美学的创造离不开军旅文学创作者这一主体。凡有军旅职业经历者多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历史传统的熏陶、训练任务的磨砺、军营生活的烙印,乃至攸关生死的考验,都会对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潜在而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套带有军人特殊性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观念上升为一个军人特有的完整哲学思想体系,我们称之为武德。军旅文学美学尽管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外部形态,但其思想内核却必须建立在武德哲学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军旅文学美学主体创造的基本途径:首先是军旅生涯的历练(修养),然后是价值观念的形成(武德),最终是美学风格的创造(铸美)。
自古而今,写出传世军旅文学作品的人,多有戎马生涯经验。须知,军旅文学当中所透露出的血性、激情、刚健、雄浑、豪壮是无法学来的,也无法模仿。毛泽东最优秀的军旅诗词大多诞生于中国革命最艰难、革命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李白和毛泽东的两首《忆秦娥》 (李白《箫声咽》,毛泽东《娄山关》)。两首词韵脚一样,但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郁。毛词情景交融,要略胜李词,尤其是结尾八个字,李曰:“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但毛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其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均比李词有过之,这大概也是因为毛泽东的战争人生体验为李白所未有造成的。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写诗。
军旅文学之美往往诞生于生与死、血与火的残酷考验之中,而不是诞生在故纸堆、图书馆里,寻章摘句、皓首穷经是无法成为军旅文学美学创造的正途的。这也是为什么军旅文学能够在中国文学大河中自成一脉,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类型文学传统(如文人传统)的独特传统。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以90岁高龄推出长篇小说《牵风记》,深刻而诗意地反映了70多年前他追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场经历。在艺术上延续了作家悲悯隽永的风格,在精神领域则持续思考战争与人性等重大问题,且均有相当突破。究其原因,这与他的战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是生与死、血与火将徐怀中带到了别人难以到达的历史深度和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
军旅诗人朱增泉说过一句名言:“我是军人,不是诗人。”细细品味其中深意,他更看重自己的军人身份。否则,也不会在近70岁时还要花整整6年工夫写出5卷本长篇战争历史散文《战争史笔记》。他的参战经历和从政经历给予他的军旅诗歌、散文美学风格的滋养,成就了朱增泉创作独特的军旅美学风格。他异常珍视中国文学大河之中军旅文学这独特一脉,自觉地以继承和弘扬这一血脉为己任,有意识地不让自己的诗歌、散文沾染上随性、柔弱、逼仄、感伤、厌战等习气。我们并不排斥军旅文学借鉴和吸纳新的资源,但过度的文人化、学院化、西方化却不能带来中国军旅文学的真正繁荣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化”上下功夫,在为我所用的时候坚持军旅文学的特殊性,不能任“去军旅文学化”倾向大行其道。
一种美学风格总是有着哲学底蕴的支撑。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表现出沉郁风格,与他感时忧国的思想境界密不可分;岳飞诗词中所流露出的激愤之情,也是他的理想与现实相冲突的产物;毛泽东雄浑豪迈、宽广瑰丽、桀骜不驯的词风,与他本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息息相关。因此,坚持和弘扬军旅文学美学的中锋正笔,就必须有健全的武德修养。
《孙子兵法》提出了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原则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价值之中“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又强调了战争的最终目的。我们在对其进行整体把握的时候,不能仅仅落脚于“不战”,更应认识到这个“不战”背后要有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谋划的总体战略意图,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支撑,更要有将士用生命和无坚不摧的强烈求胜欲望为保证。因此,“不战”与“伐谋”“贵胜”不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砥砺,彼此更加强健而有所作为,这是民族性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武德修养的真正血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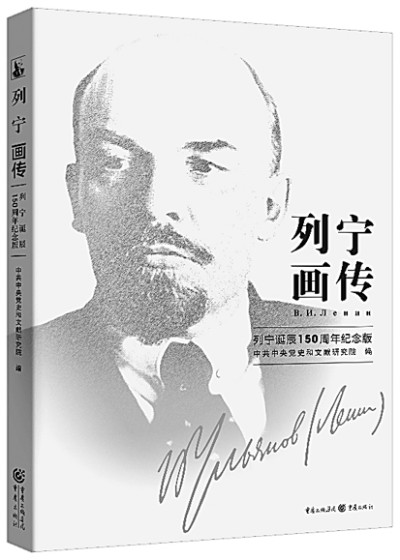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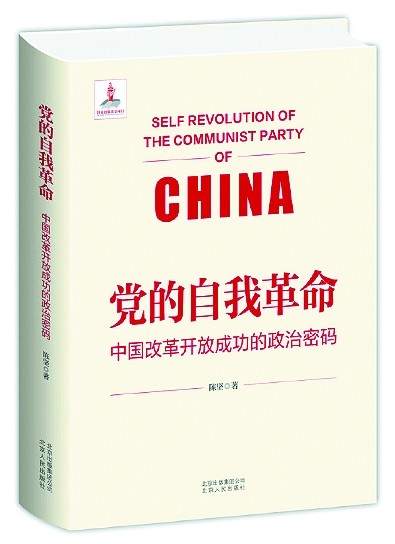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