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神话是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不可复制、不可替代,成为认知各民族早期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凭据。然而,神话的价值不止于此。除了填补历史文化记录空缺的作用外,神话的其他价值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就是神话作为文学的种子,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与西方神话相比,中国神话散见于各类典籍中,体系上略显不完整,规模上也不够宏大。这给中国神话的系统研究带来不便,但无形中却给神话种子在文学园地的再生和茁壮成长减少了障碍,为神话的文学演绎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由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拙作《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正是一本重在探流,把神话作为一颗颗文学母题的种子,去深入挖掘梳理这些种子在后代生根、开花和结果的繁荣景象,展示中国神话文学完整风貌和成就的书。
一
神话是史前先民历史文化的零星记忆。文字出现后,人们把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记录在不同文献中。这些文献依据时间和性质不同,可分为原生性神话文献和再生性神话文献。
原生性神话文献是指先秦时期最早用文字记录神话内容的文献,其时间上距离神话产生的时间最近,基本上源于口耳相传,以《山海经》保存神话故事最多,其他如《诗经》《楚辞》等文学总集,《穆天子传》《尚书》《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归藏》《古文琐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文献中,也不同程度保存了大量神话。这些记录尽管零散,但大致构建了中国神话的基本框架和原型规模。
再生性神话文献发端于秦汉,至明清一直有出现。从时间和属性上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秦汉时期文献。这一时期尽管已经远离神话产生的时代,但因距先秦较近,仍能约略窥见神话的原貌。对神话的记载,见诸《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等杂史书,以及《论衡》《风俗通义》等子部文献和大量纬书中。这些文献性质不同,摘引神话各取所需,其中有些内容与原生性神话文献吻合,有些则不见于原生性文献。虽则如此,它们对神话的原貌仍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第二类为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文献。这个时期离远古更加遥远,相关记载的文献属性淡化,内容可分两种:一种是作为文献保存,抄录前代记录的材料,见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量类书。第二种则为中国文学独立之后,依赖于诗歌、散文、词曲、小说等各种文体的繁荣,将神话作为题材的各类文学创作。它们为中国神话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为古代神话的再生创造了繁花似锦的园地。
因此,从文学再生角度关注中国古代神话,可成为以往神话历史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外的新视角、新视野。
二
神话在中国文学土壤的演变,大体随各种文体的形成和流行情况而生发、成熟。
中国叙事文体的成熟大大晚于抒情文体,因此作为抒情文体代表的诗歌,是神话文学再生时间最久、内容最丰富的领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楚辞》,含有大量神话故事要素。进入汉代之后,神话母题、题材很快有了蔓延和滋长。汉代乐府诗中有大量神话题材内容,《古诗十九首》中关于牛郎织女、王子乔的神话描写,是诗歌对神话进行文学描写渲染的开始,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路。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开始铺开笔墨,大量吟咏神话题材。陶渊明《读〈山海经〉》用十三首诗歌颂精卫、刑天等神话人物的精神。诗歌进入近体时代后,神话在诗歌中出现两条轨迹,一是作为题材,二是作为典故。前者如顾炎武《精卫》,后者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蚕丛鱼凫,不可胜数。
从散文角度看,汉赋不仅受到楚辞文体影响,而且也继承了楚辞擅用神话作为铺排典故的传统。从扬雄《太玄赋》《蜀都赋》,到班婕妤《捣素赋》,桓谭《仙赋》,都以铺排大禹、王子乔等神话人物的方式增强文章的气势和宏大的结构感。这个传统也一直延续到后代的赋体创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晋时期左思的《三都赋》。
作为叙事文学文体的小说戏曲产生、成熟晚,但在让神话的种子在文学的领地开出灿烂的花朵方面,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张华《博物志》等笔记小说中,保留着两汉诸子和史传文章转录早期原生性神话文献的痕迹。到了唐代传奇,就完全抛开原生性神话文献“丛残小语”式的零散记录,代之以驰骋想象。杜光庭《墉城集仙录》笔下的瑶姬神女帮助大禹治水的精彩描写堪称范例。而明清章回小说问世后,又把神话的文学再生创造推送到极致的境界。在渲染神话形象故事基础上,发挥结构优势,把神话题材应用于整部小说。李汝珍《镜花缘》大量采用《山海经》的材料,巧妙构思,另起炉灶,用文学手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文学神话世界。中国文学扛鼎之作《红楼梦》,全书结构以僧人所携顽石下凡的那块通灵宝玉所贯通,正是女娲补天这一神话的馈赠。受此构思影响,晚清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将女娲石隐喻为救国女子,贯通全书,赞美女性救国。可谓前呼后应,琳琅满目。
三
中国神话的文学再生过程跨越汉代,延绵至晚清,前后两千多年。其间,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影响和制约了再生过程,同时也使再生成果成为展示各时期文化价值和取向的窗口。
神话文学再生的突出文化价值是承续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中,饱含的战天斗地的雄心、意志和勇气,在后代文学的创造中深入人心,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其次,神话的文学创作,不断被历史上各种文化的母体作为展示弘扬自己精髓的方式。汉代的纬书中,已有不少内容以神话材料宣扬谶纬思想。佛教、道教等宗教思想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往往借用神话材料,采用诗歌、小说等载体方式影响大众。西王母神话原型在后代不断被道教文学所引用,就是一例。
其三,神话的文学创造,将神话原型中先民所寄寓的理想,用文学手法加以放大和升华,使其成为后世的追求。七夕鹊桥、牛郎织女在后世各种文学体裁中反复出现,成为亘古爱情的化身,便是这种价值的体现。
另外,神话文学再生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受古代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的制约,也出现过一些价值判断模糊,甚至逆向行走的轨迹。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样本来具有正面价值意义的壮举,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不时遭到讥讽,而原生性神话原型中女娲女王之治的母题,在后代男尊女卑思想作用下,在文学再生中遭到了扼制和湮灭。
神话文学再生问题复杂庞大。拙作《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或许可为把握中国神话的研究路径、拓宽中国神话研究的视野,探寻一点答案。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首席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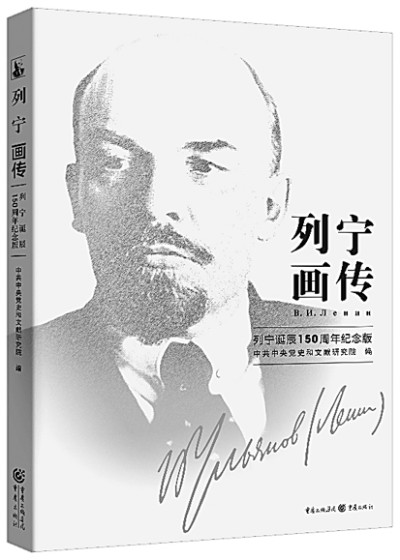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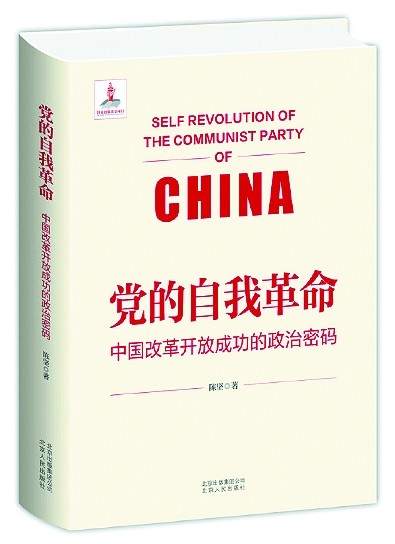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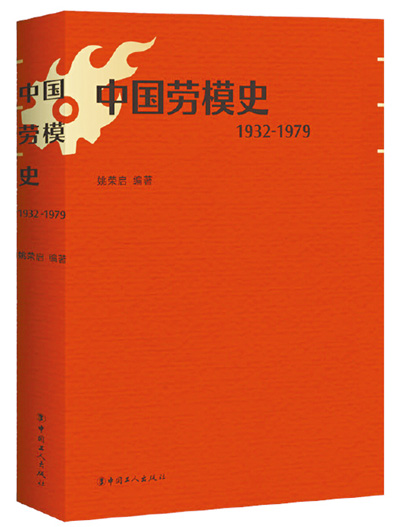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