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咏同志曾在山东调研时强调:“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诚如他所指出的:“这体现了德治的要求,也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实际上,司法应当合乎基本人情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有了“以情断狱”的观念。《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一个叫“曹刿论战”的典故,在该典故中,鲁庄公对曹刿说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答道:“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就已经非常重视“情”在狱讼审断中的意义了。而后世法学家与司法官员对“情”字的强调,也一如既往。如《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中便记载了宋代司法官员胡石壁的话:“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可见,在司法裁判中尽量保持人情与法律的有机统一,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司法理念。那么,被古今司法者所重视的这个“情”字,到底有何具体含义呢?笔者经过梳理文献后发现,古代刑事司法中所称的“情”,大致包括了这样三个层次的含义:情理,即普通人都有的基本逻辑和知识;情志,即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情感,即司法官员个人的恻隐之心。
情理:普通人的基本逻辑
“情理”二字,是研究中国法史的学者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词,清末名家沈家本与樊增祥都曾明确讲过情理之于法律的意义。沈家本说:“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所贵融会而贯通之。”樊增祥也曾讲:“情理外无法律,抱旧本者不知,讲西例者亦未合也。”从沈、樊二人的表述来看,“情理”二字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但值得追问的是:古代人口中常被提及的情理,究竟应当作何解释?很多学者都将“情理”解释为天理和人情的简称。这种解释固然经典,但问题在于,天理与人情的概念并不比情理一词更加明晰。因此,将“情理”解释为人情与天理,甚至会使情理一词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理解。笔者认为,古代刑狱审断实践中常用的“情理”一词,大多数时候都是表示古代普通人都有的基本逻辑和常识。在《折狱龟鉴》等传世法律文献中,作者曾多次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情理”一词。如《折狱龟鉴》卷四《议罪》所载“胡向科杖”一案中记道:“胡向科杖胡向少卿,初为袁州司理参军。有人窃食,而主者击杀之,郡论以死……以情理言之,则与凡人相殴击异矣。登时击杀,罪不至死也。”这里所谓的“情理”,乃是指一种常人都有的基本逻辑和判断,即主人殴打盗窃犯致死的行为要比普通殴打致死的行为在情节上更轻。另外,《双佩斋文集》卷四《癸丑八月秋审班签商二起》中的陶奉廷案里也有这样一句话:“看得陶奉廷于寡居弟妇勒索凭凌,已非一日,甚至当街批颊,毫无男女之嫌,尤非情理。”这里的“情理”,也是指常人都会有的一种基本认识,即作为哥哥的陶奉廷不应该长期欺负寡居的弟媳妇,更不应该当街掌掴她。从前述两个案例中可知,“情理”一词在连用时,并没有形而上的“天理”之意,而仅仅表示古代普通人都有的一种基本道德逻辑和事理逻辑。
实际上,中国古代律文和审断实践中所称的“情”,都是指作为一种基本事理逻辑和道德逻辑的情理,而符合情理的事实,便被称为“情实”。 如《折狱龟鉴·曹摅明察》载:“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实,时称其明。”这句话中的“情实”二字,即是指的符合情理的事实。当然,也有很多律文中将“实”字省略,直接用“情”来指代符合情理的事实。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所载“无笞掠而得人情为上”中的“情”,《宋刑统·断狱律》所载“须别设法取情,多方辨听,不得便行鞭拷”中的“情”,都是指通过基本情理检测后所得出的事实真相。
情志:嫌疑人的动机目的
除了情理这一层含义以外,古代狱讼审断语境中的“情”,还有“情志”的含义,这里的情志特指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动机与目的。
中国古人在听狱的时候特别注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春秋繁露·精华》中载:“《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这句话是董仲舒原情定罪主张的经典语录,从“原其志”三字中可以看出,以他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对犯罪主观方面的极度强调。这一观念对传统中国人的断狱观影响至深至远,直到清代还有人将这一理念奉为断狱圭臬。如清人黄六鸿便曾说:“凡拟人之罪,最贵原情。事有关于纲常名教,或强盗叛逆、为法之所不容贷者,是其犯罪本情,原与人以无可贷……如孝子为亲报仇,或报之数日之间,或报之数年之后……此事关纲常伦纪,而情有可原者也。”黄六鸿论述中的“情”,与董仲舒所说的“志”,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都是指犯罪嫌疑人行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
情感:司法官员个人的恻隐之心
“情”字除了指代作为普通人基本逻辑的“情理”和作为嫌疑人行为动机的“情志”外,还常常用来指代审讯者和断狱者的恻隐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很多现代人对“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行为深恶痛绝,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曾是儒家学者的大体主张。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通过与叶公的对话,明确表达了父子应当相隐的观点;而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通过与桃应的对话,也明确表达了虞舜应当窃负而逃的观点。这些观点从本质上看,都算是一种“徇情枉法”的主张。只不过,在儒家的语境里,他们不惜枉法也要维护的那种情感,并不是一种过度泛滥的情感,而是指人的基本情感,如亲子和夫妇之间的亲爱之情。而这些情感在儒家知识分子眼里,是每个人都有也应当有的恻隐、不忍和仁恕。这种被儒家知识分子认为是非常正当的情感,也被逐渐带进了刑狱审断过程中。如唐代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在审理青州一桩谋反案时曾说:“尝闻理狱之礼,必务仁恕,故称杀人刖足,亦皆有礼。岂有求身之安,知枉不为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愿也。”崔仁师所谓的“必务仁恕”,可谓儒家式情感主张的极佳解释。
综上可知,古代刑狱审断语境中的“情”字,至少包括了三层意思,即普通人的情理、嫌疑人的情志和司法官员本人的情感。纵观历史,中国古人对“情”字的重视与发挥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司法领域,并贯彻进了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代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更是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归为了一个“情”字,由此形成了他本人情有独钟的“情本哲学”。可见,“情”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形而下的司法意义,更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在司法实践已经日趋深入的当代中国,要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不妨对深藏于人民群众心中的公正之“情”有一个更为深入的思考。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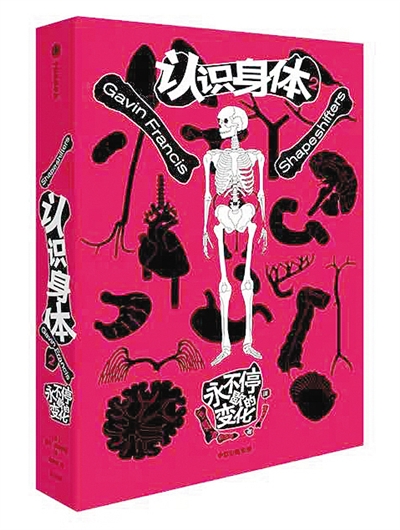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