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各地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发生频率和种类大增,SARS、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以及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陆续给人类的生命安全与生活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失。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基因的相似性,人类许多新发传染病都于动物有关。因此,改进和健全动物防疫立法,对巩固防控疫情防线,提升动物卫生水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推动我国动物防疫工作从“救火”状态转为常态化的系统保障机制十分关键。
我国现行《动物防疫法》由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后经2007、2013、2015年三次修订。但有些方面仍不够完善,相关部门法之间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一、《动物防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对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动物诊疗、畜产品卫生质量等方面没有规定;二、《动物防疫法》仅适用于对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管理,缺少对动物及其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卫生监督,也缺少对兽医工作进行有效监管和服务保障;三、部门法规之间的有效衔接不到位,动物防疫相关立法间的系统性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譬如,《动物防疫法》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在职能界定上有的地方出现交叉,有的地方又出现脱节,不能适应国内外新形势下动物防疫工作的开展。由此,要保障动物防疫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动物防疫机制的有效运转及对防疫工作的有效监管,让法律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尽快修订完善动物防疫立法。
2020年4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这一草案是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委员会在充分结合国内外疫情防控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望在以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其一,强化动物防疫责任。强化生产经营者的防疫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和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有鉴于病源疫情发展科学原理,压实属地责任,防止因经济利益等其他因素的瞒报不报和迟报;加强直接汇报机制,在现有汇报直接管理通道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防止出现“你管、我管、他管,出事没人管的现象”。明确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合作,避免“八个部门管不了一头猪的现象”。
其二,建立健全动物防疫管理制度。强化对重点动物疫病的净化、消灭,在全面防控的基础上,推动动物疫病从有效控制到逐步净化、消灭转变;强化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动物的检疫检验。同时,严格利用野生动物审批制度,将动物专业交易市场纳入动物防疫条件审查范围;建立伴侣动物、流浪动物、可饲养野生动物等动物免疫强制接种制度;实行饲养动物耳标制度,加强饲养环节兽医卫生服务管理。逐步改变民众活禽消费习惯,全面禁食野生动物。
其三,完善动物疫情风险管理制度。健全防疫机制,实行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程化监控。将动物防疫工作覆盖到饲养、加工、运输、贮藏、销售到餐桌的全过程。增加畜产品卫生安全和突发疫情应急等内容,充分发挥动物疫情风险评估机制预警干预的实际效能;强化以服务代管理的预防意识,将重点动物疫病净化、消灭补助及管理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和监管;出台配套法规和规章,确保检疫防疫和动物源性食用的安全监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实践。在完善立法的同时,也注重严格执法。
首先,“法之不行,甚于无法”。法律得不到执行,就不可能具有公信力并得到普遍的遵循。而动物防疫法律如能得到严格执行,因食用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就可能在最大限度、最低成本内得到控制。
其次,突出执法主体责任。既要通过法律的实施,推动动物防疫服务管理制度的完善,促使动物防疫执法主体能够依法履行公益职能和技术服务职能;也要进一步提升兽医药服务管理水平,依法规范执法主体动物防疫监督、检验检疫、残留监控等具有明显公益特点的政府职能行为。此外,应强化基层防疫执法队伍,目前的执法责任有相当一部分由乡镇兽医站或者带有经营色彩的事业单位履行,执法单位一方面要执法,一方面还要从事诊疗和经营活动以维持其收入,致使执法监督工作创收导向明显,削弱了执法主体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不能提升有质量的社会服务。
最后,强化基层防疫服务保障水平。一方面,要坚持以服务换管理,将服务保障工作做到位。将重点动物疫情病原化、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等纳入政府公共财政范围,发展畜禽养殖保险,加大对技术创新研发的鼓励和支持力度,提高基层动物防疫人员的福利待遇和技能培训水平。另一方面,要真正做到防疫重心下移,防疫资源下倾,防疫权力下沉,保障基层参与防疫人员的数量和待遇。夯实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努力提升动物疫病控制和畜产品安全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作者: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杨静,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王斌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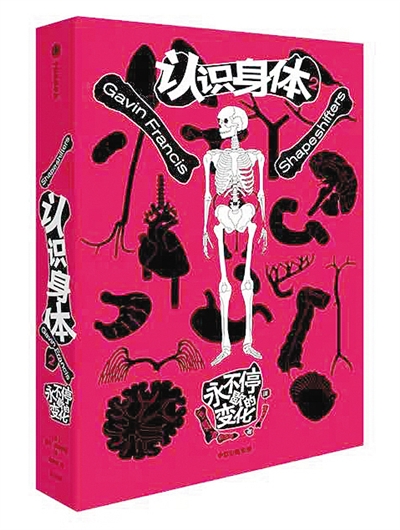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