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唐朝,就来到了宋朝。当此时,不禁想起所谓的“唐宋变革说”。
把整个历史时期分成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是西洋史研究所惯用的。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首次将这样一个“三分法”运用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并且提出了一个“唐宋变革说”。在《中国史通论》一书中,内藤湖南认为:“在唐宋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古与近世的差别。从这一点而言,中国的近世时期可以说自宋代开始。”那么,宋代中国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近世社会的特征呢?另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列举了以下三点:成为经济统一体,新文化快速发展,国民的自觉意识也开始萌动。
与此相应,宋代的法制也表现出与唐以前不太一样的样貌。例如,唐代的法学世界观基本是承袭汉代而来,并无太多的创新和突破,而宋代却诞生了更为细密的理学世界观,并对元、明、清各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 “宋代法典之多,实前古所未闻”。就像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所说,“盖终宋之世,迨靡岁不从事于编纂法典之业”,“亦可谓集千古之壮观矣”;又如,在宋代,还出现了较为发达的法医学(例如宋慈的《洗冤集录》)和判例法研究(例如郑克的《折狱龟鉴》)。因此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达到最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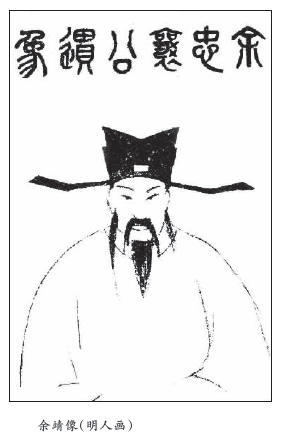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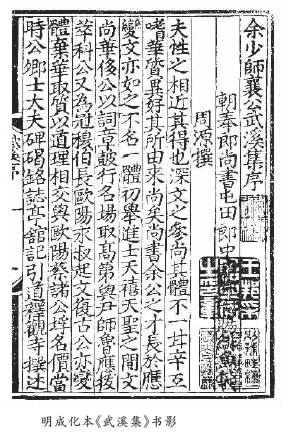
说起宋朝的新气象,不能不说说印刷出版。西方有句名言:“没有古腾堡就没有宗教改革。”古腾堡是德国美因茨人,由于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机,而使得《古腾堡圣经》能够实现“日传万纸”。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木版印刷,就没有唐宋变革。”正如日人小岛毅所指出:“世界上最早盛开印刷出版文化之花的是宋代……印刷物的普及,把人类自古以来的智慧播及街头巷尾。不仅新发现、新发明,包括唐宋变革本身,也与文化的普及密不可分。”法律也是如此。宋代以前的律典都是写本,只有到了宋代,新旧律典才开始被雕版成书,法律的普及也才成为可能。
印刷出版的普及也给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带来深远影响。仁宗天圣四年,朝臣孙奭说:“诸科唯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举人难得真本习读。”仁宗因而下诏刻版颁行。在北宋中叶,法律读物甚至走向了村校。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南宋桂万荣在担任余干县令时发现,“今吉、绮等府书肆有刊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宋末周密的《癸辛杂识》则记录了民间“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
宋代的科举也有变化,不仅将竞赛选手扩大到了社会各阶层,而且,法律考试的种类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较之各代,也是首屈一指。不仅设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而且还有“明法”“新科明法”“试刑法”“呈试”“诠试”等等名目。即使是进士、武学、算学、画学等科目,也要试律断案,并且不再像唐代那样,一味强调“文理优长”,而更注重“引律入题,准法析理”。这一点,恰是与近世文化的演变同步的,其突出特点是,由重形式日益走向重内容;由过去的贵族文学,变为庶民的东西。
前述所有“近世”色彩,都是促成宋代判词变革的社会文化基础。宋代的代表性判词,收录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它不仅是判词史上第一部实判专集,更是宋元明清各代判词文体的滥觞之作。其主要特色是,在文体上,它一扫唐代判词的骈俪堆砌之风,“文皆散行,绝无俪语”;在内容上,则注重说理,引律为判。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谓:“是宋人判牍之体,与今人同。”换句话说,到了《清明集》,最为接近现今体制的判词终于出现。日人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一书中更是认为,《清明集》的明代刊本被发现后,立即“在全世界的宋代史研究中掀起了一场‘清明集’热”。我自己品读之后也认为,《名公书判清明集》堪称古代判词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
罗马不是一夜建成的,变革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名公书判清明集》并非在宋初即已出现,而是到了南宋才得编纂而成。一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所言:“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这个“余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仍像唐判那样“以俪偶为工”。不过,据许同莘《公牍学史》考察,在宋代,“其以俪偶为工者,惟科举试判词沿唐人成式耳。官司常行文牍,实不如是。”北宋时期仅见的一部判词集《武溪集》,就是试判之作,也一仍骈四俪六之体,尽管如此,却也有了与唐代《龙筋凤髓判》和《甲乙判》所不同的样貌,就连不太喜欢骈判的洪迈都说它“粲然可观”。所以,在品评《名公书判清明集》之前,我们不妨先领略一下这部判词的风采。
《武溪集》的作者是余靖。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自少博学强记,天圣二年举进士,天圣八年试书判拔萃。入仕四十年,敢言直谏,司职甚勤,虽沉浮宦海,但有死不避。官至工部尚书,赠刑部尚书,谥曰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余靖就是以范仲淹“朋党”的身份而名闻天下。宋仁宗景祐三年,爆发了一场“朋党之议”,范仲淹因“言事无所避”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被罢去权知开封府职务,远谪饶州。谏官、御史对此均不敢言,三十七岁的集贤校理余靖却第一个站出来为他上书鸣不平,结果也被贬为筠州监酒税官。被定为“朋党”相继被贬的,还有尹洙和欧阳修。时任馆阁校勘的蔡襄为此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传播极广。所谓四贤,指的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后来,重返阙廷的余靖又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辅佐仁宗,推行庆历新政,不意复又遭人谗毁,重演朋党之灾。欧阳修为此曾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其云:
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
余靖与范仲淹、欧阳修,就属同道、同心。范仲淹的人生准则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欧阳修为余靖所撰墓志铭则云:“公为人资重刚劲,而言语恂恂,不见喜怒。”虽然余靖的诗文不比范、欧,但作为能有判词行世的北宋唯一之人,也足可笑傲青史。
还是来说说他的《武溪集》吧。这部文集,是由余靖之子、屯田员外郎余仲荀为父编成。至于书名的来历,丘浚所作明成化本《武溪集》序云:“岭南人物,首称唐张文献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夹城流,自泷来者曰武溪,浈水自庾岭下,与武溪合,是为曲江。张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盖有意以匹张欤?”《武溪集》体裁广泛,诗、序、论、记、制诰、表、启、杂文、墓志、奏议,不一而足,其中判词则有两卷,合计51篇。黄志辉在《武溪集校笺·前言》中说:
余靖现有的判词,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御试、秘阁试和私试的原貌。举凡诗礼教化或政经刑法,其所应对,均事著典章,理资沿革,随手拈来,是非互见。贵在识时度事,不袭常规,顺变从权,协于大中。不但研究宋代法制史可资参证,也是古代文体学不可多得的教材。
我们选取其中的两道判词以为欣赏。其一是“拷掠弗承判”。制判事实为:“庚为狱官,拷囚数满不承,欲取保放之。法司云:‘赃状露验,宜据状断。”判曰:
拷掠弗承,诚宜判遣,赃状或露,亦可稽详。苟再思而不疑,在两端而必叩。庚也职司丛棘,伏念幽囚。缧绁之中,五听备研于辞色;捶楚之下,三讯未穷于是非。眷兹狱法之官,各以律令为据。司圜以搒笞既极,不加刑焉;执宪云踪迹可寻,断斯狱矣。然则五毒备至,有词者难俾伏辜;九章甚明,隐情者不宜免戾。至若事必先于审克,罚无疑于滥施。昔汉祖柏人,贯高被刺肌之痛;楚相亡璧,张仪沦刻骨之冤。皆出狐疑,终闻开释。若乃杀人者既彰实状,坐赃者已获见资。且明白而可知,谅结正而无枉。非此物也,胡可比焉?理贵从宽,法难任意。
本案涉及的是刑讯逼供,这是一个绵延于整个中国法制史的古老话题。刑讯起源于何时?《史记·李斯传》里就有他被“搒掠千余”的记载。《汉书·路温舒传》则说,路温舒在汉宣帝即位时上疏:“夫人情安则乐生,病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因此通说认为,“后世讯囚用笞杖盖从汉律也”。“讯刑”被视为“中华法系的癌”,停止“讯刑”之议也代代皆有,但正如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所指出的:“老实说来,就在民国成立之后,‘讯刑’也并未完全消灭。”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千余年前,余靖就对“讯刑”问题有了理性之论:“缧绁之中,五听备研于辞色;捶楚之下,三讯未穷于是非”。“五毒备至,有词者难俾伏辜;九章甚明,隐情者不宜免戾。”行文虽仍属四六骈俪,却句句说理,迨无藻饰。
其二是“欲从轻法判”。制判事实为:“狱囚未断而格令新改,法司引后敕为正。判云:‘犯时格轻,新令稍重,欲从轻法’。”判曰:
沿革异宜,虽遵后命,俘囚待弊,必从轻典。当顺以宽之教,庶廓在宥之怀。眷彼庸材,齿于编户。出作入息,方承荡荡之风;恶稔贯盈,遂陷恢恢之网。聿罹昭宪,乃寘圜扉。词置钩金,将成于具狱;令行徙木,忽改于旧章。既丹笔之未书,故两端而起议,将垂经世之范,犹疑在禁之人。宪司以其命惟新,何可废也;从事以惟刑之恤,不已重乎?再详抵禁之初,方当改度之始,刑必当罪,法宁与人。且除旧以布新,虽宜舍旧;奈先轻而后重,姑合适轻。令式具陈,古今共贯。纵利百而变,弗取乐成;稽画一之规,固闻前定。俟其来犯,乃用新书。
本案涉及的是刑法适用中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有研究者认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法律的溯及力问题并未得到重视,直至清朝末期,相关内容才见诸于法律文件之中。”其并举例说,宣统二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第一条确立了刑法向后生效的原则,并允许有利于犯罪者的溯及既往。但在本道判词中,余靖就相当充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沿革异宜,虽遵后命,俘囚待弊,必从轻典。”“且除旧以布新,虽宜舍旧;奈先轻而后重,姑合适轻。”逻辑严谨,法味儿十足。而这一切,都是“刑必当罪,法宁与人”这一法律哲学之下的必然产物。
善四六、工辞华,《武溪集》确存有唐之余波;懂专业、爱说理,余襄公又实为《清明集》诸名公之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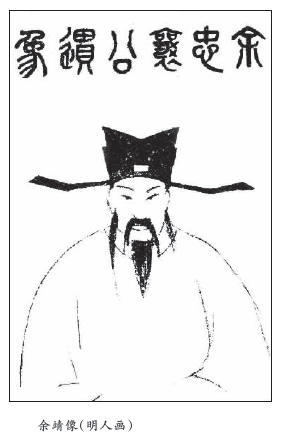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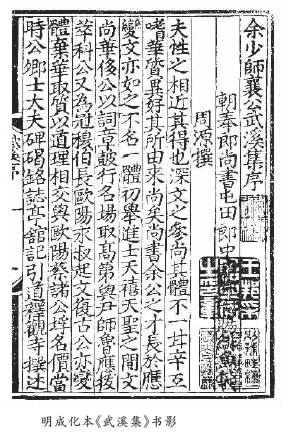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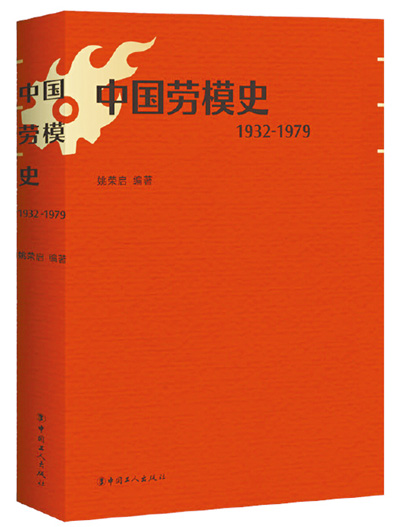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