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疫情考验各国应急与组织动员能力
彼得·柯西尼:新自由主义理念将一切私有化,尤其是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摧毁了人们积累的资产基础——将社会资本从底层转移到顶层,转移到西方私人银行和少数寡头手中。这就摧毁了较贫穷国家可能好不容易建立的、为数不多且往往脆弱的社会安全网——原本安全网能够在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贫困激增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中国愿意与世界分享其巨大的发展成果,这与西方的一贯做法相反。中国选择合作而不是竞争,受利润驱动的西方资本主义很难理解这种概念。
中国从70年前的零基础出发,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社会主义成功的生动例子。中国是从不寻求冲突或侵略的国家,是努力发展伙伴关系并提倡和平共处的国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和平和双赢,搭建各国人民之间的桥梁。这是21世纪发展的基石,它标志着不同条件下的全球化——基于平等的全球化。伙伴国家是在邀请而非胁迫下参与这项伟业,以陆路和海上路线跨越世界,开展贸易等各种交流,为新技术和社会科学带来源源不断的想法,推动人类和平互动。

8月26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医务人员为一名儿童做新冠病毒检测采样。新华社发
黄平:我们正在见证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本身成了最大的确定性,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制度失灵、安全失控、精英失职,在西方国家已不是个别现象;国际关系重组、国际秩序重建、国际格局重构,是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论人们愿意不愿意。2020年又平添一大变数——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围绕疫情的诸多流行病学问题仍无确切答案,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停摆仍未结束。
迄今我们所知所熟所用的国际层面的制度、机制、组织,更多的是二战结束后为了防止人类再度陷入战争,为了在和平基本能维护的环境下谋求经济社会发展,而很少是为了预防和制止病毒大流行,连这方面的专业人员、预算经费、组织架构、体制机制也都相当薄弱,在有的国家甚至形同虚设。这给有效抗疫增添了难度。概括起来,第一,这次疫情暴发,所有人和国家、政府、组织、机构,谁都没有先见之明、提前知道,更没有提前知道如何妥善应对,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无端猜忌别人一开始没有采取更高明的措施,更没有资格去事后诸葛亮般地指责别人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第二,这次病毒降临,对所有人和国家、政府、组织、机构,都是一次大考,经受考验的,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实际的应急与组织动员能力,尤其是面临紧急的公共卫生危机时的应急能力和治理能力,其中包含但不限于:国家的组织力、民众的配合度、社区的管理水平、个人的行为自觉、防疫体系的健全性与可行性、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与奉献精神,等等。第三,这次疫情蔓延,使本来就还没有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的各国经济变得更加低迷,失业人数之多已经成了某些大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故也无法从原有版本的经济政策中直接找到解困之道,包括试图逆全球化而上,不仅要自我“优先”,而且不惜单方面“脱钩”。最后,这次抗疫对所有人和国家、政府、组织、机构,都是全新的挑战,使本来就已经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使我们本来就面临认识范式与治理方式转换的巨大压力变得更加沉重。
王灵桂:一个时期以来,全球化到底还有没有前途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其中,美国因素是造成人们困扰的主要原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对外政策由全球扩张向孤立主义回调;美国正在失去领导意愿,又不愿意别国发挥某种补充作用;随着国际新生力量的不断崛起,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构建的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体系在保障其实现自身利益方面的效率,其政策取向由“全球模式”向半封闭乃至封闭的“俱乐部模式”转变;美式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观和国际规范,强调美国样本的普世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西方主流价值观遭遇质疑,西方社会分裂加剧,既体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也体现在保守力量与自由主义建制派的政策分歧,还体现在精英阶层与公众之间的认同分歧和矛盾。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的所谓“逆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政策犹疑和多变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个特征在当前抗击疫情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疫后的全球化将不会再是美国一家独大,而是多种力量共商共建共赢的格局。

黄平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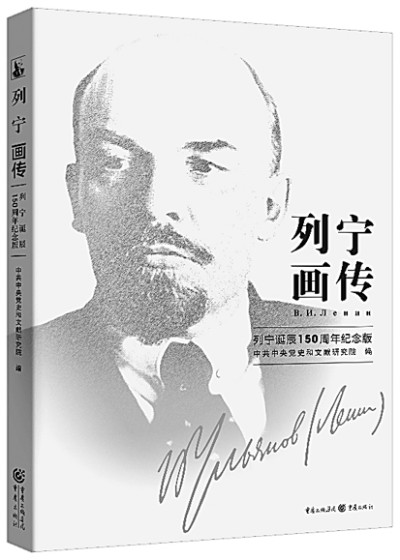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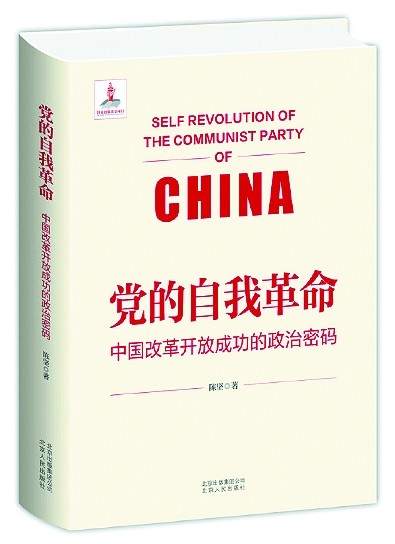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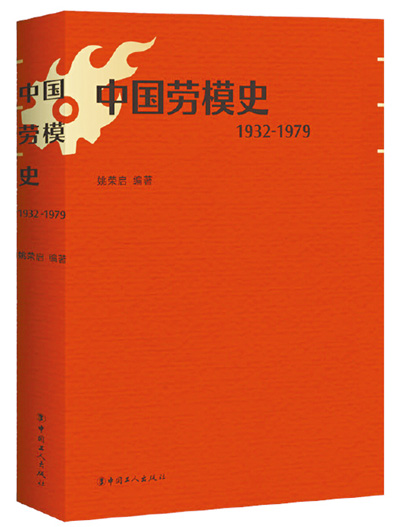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