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高效能治理需要结合高质量发展要求,针对新形势与新任务,对治理理念和方式进行深刻调整。
坚持“惠而不费”“威而不猛”理念,善用传统政治文化精髓搞治理。高效能治理的关键不是效率,而是效能,效能必须兼顾效率与成本,牢固树立治理的成本意识,清晰意识到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大道至简”“惠而不费”“威而不猛”的哲学,孔子告诫君子要给百姓以恩惠而自己却尽量耗费,要在施政中展示威严但并不表露权力凶猛的一面。从传统治理实践来看,中国的历史传统往往善于在国家财税汲取能力不高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政治成本和社会成本解决广泛的治理问题。这些哲学思想和治理传统,对于思考高效能治理的概念、克服治理实践中的弊端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避免“四面出击”,集中优势力量落实重大部署致力攻坚破难。任何改革和治理都要有战略重点、优先顺序和主攻方向,如果政策设计过于繁重复杂,层层加码后落到基层,必然带来“多任务”管理体系的通病,即在时间、人力和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执行层无暇聚焦核心力量、落实核心任务,多任务管理变成了胡乱应付,最终造成改革部署难以落实。历史经验显示,越有发展压力,越要保持改革定力,越要树立制度成本和资源成本意识,在治理中要避免四面出击,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当时外部帝国主义封锁、内部阶级斗争加剧以及各方面困难日趋显现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他提出,面对复杂形势不能目标太多、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以便于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针对当时社会领域的改革,毛泽东同志提出改革不能急躁,条件不成熟不能改革的策略。这一方针为当时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稳定社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今天一些地区的改革中,就很好地坚持了这样的方针策略,以脱贫工作为例,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一些地区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集中优势力量一鼓作气、攻坚克难,确保全面完成脱贫目标任务。
重视协商共治,围绕治理难题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新时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急需调动更广泛的政治积极性和社会积极性,形成了一对内在矛盾,需要深刻把握发展的节奏。高效能治理下,制度威力和制度效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必须依靠各级各类机构和广大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好的政策要落实,首先需要人们理解制度、尊重制度,自觉在制度框架内做事,需要创造制度实施的前提条件,并能够根据不同条件和时机因地制宜采用适宜的执行方式,改革的整体性革命性和复杂性联动性,要求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针对治理领域出现的碎片化、割裂化、条块化等短期行为,以及各领域改革中不配套不协调、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相互抵触等问题,除了加强机构设置和制度运行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外,还需要鼓励体制内部横向、纵向各级各类机构之间沟通协调会商机制的完善,通过激活内生信任,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立足国情世情,尊重发展的差异性与层次性需求。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得到不断发展和深入推进,但是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依然显著,发展的差异性格局和治理的层次性需求将长期存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期,我国国家治理将不仅担负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继续推动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任务,而且要面对较充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治理挑战,包括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难的任务,以及协调不同性质、不同主体和不同层次利益关系的任务等。高效能治理是对治理的科学规划和分类基础上的治理,2020年疫情之后政府将“保就业”“保民生”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就体现了对发展阶段性的尊重,反映了治理的层次性要求。与此同时,针对那些工业化城镇化比较充分、收入较高的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不仅期待更高的治理效率,而且对于治理的形式和公共产品供给多样性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适度增强“弱中心”思维,培育软性权力特征的治理系统。面对高度异质化的治理空间和高度复杂性的治理任务,高效能治理需要更多具有“软性”权力特征的治理主体和治理系统的参与,国家治理的“软件”系统支撑的问题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软件”系统的核心是去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管理,是资源的智能化配置与分布式管理,大幅度压缩管理层并降低行政和制度运行成本,是可以预期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此次疫情为例,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参与疫情防控,是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未来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公共数据管理将加速从封闭逐步过渡到有效开放,完全中心化决策将逐步释放给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将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从而弱化政府直接参与管理和监管的能力。新兴技术群体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高效能治理无法脱离技术群体的广泛深度参与和支持。与此同时,也需要及时启动新技术主体协同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与相关规划,加速推进数字化政府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公共治理的制度规则,有效加强监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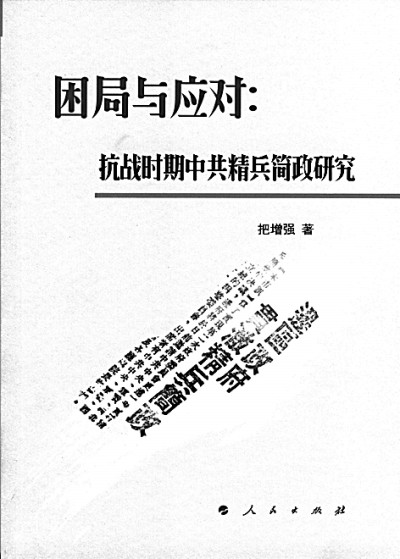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