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奠基者、我国德育理论研究的持续领跑者;
她,是新世纪我国小学德育课程与教材建设的设计师、深受学生爱戴的导师;
她,就是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当代教育名家、全国教育科学突出成就奖获得者、江苏首届“社科名家”、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鲁洁先生。

>
学人小传:
祖籍四川阆中,出生于上海。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学家,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教科所所长、教育科学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德育学科组组长、全国德育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
长期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学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体系。合作编写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获全国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与王逢贤共同主编的《德育新论》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持第八次课程改革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研制,任国家统编教材小学《道德与法治》总主编。领衔的“小学德育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个人自述:
我是从事教育和德育研究工作的。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不但要关注人的现实存在,更当瞩目的是人之可能,需要我能够触摸到人身上最具人性、最为美好的部分,并通过教育而使它成为生活中“普照的阳光”。“人本来是可以这样美好的,教育的神圣使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可以’而努力。”它已经成为我的教育信念,我会坚守我的信念一直走到人生的尽头。
童年:
在书堆里长大,埋下智慧的种子
记者:您出生于书香门第,父母的教育对您的一生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鲁洁:我1930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今年刚好90岁。父母的良好风范与教养给予我一生许多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书本、对知识的挚爱,像我这样在书堆里长大的人,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本伴随着我的整个求学经历。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爱书如命,对知识探究有一种热忱。母亲也在上海接受过当时最好的教育,很能干,能烧菜,会做西式的蛋糕,会裁衣服,能自己编织,她那一代人在生活情趣等很多方面超过我们这一代人。母亲虽然呆在家里,但一直关心国家大事。直到80多岁去世前,她还每天都看《参考消息》。我们家里面姐弟三人。姐姐后来英年早逝,我很伤心。直到现在,我还会怀念她,怀念我们的手足之情。我和哥哥是欢喜冤家。长大以后,哥哥的兄长情结很重,很照顾我。有兄弟姐妹,不但可以拥有手足之情,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激发智慧的空间,就算是跟哥哥姐姐吵架,那也是很长智慧的。现在我觉得,家庭教育基本上不是语言的教育,而是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孩子。
父母在对我的教育上比较开放,学校里面的老师对我也比较宽容,使我这个从小调皮捣蛋的“另类”学生,能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回想起来,我走的每一步,父亲都给我一个合理化的解释,他从不给我否定的解读。父母的期待和支持,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学校老师对我的爱与宽容,我至今仍然记忆深刻。
在我小时候的生活中,与自然亲近,是我的一个特点。在我的童年时期,我的生活里有树木,有花草,有鱼,有虫;我养过小猫、小狗、小兔;我抓过蝴蝶,抓过蚂蚱,抓过小鸟,抓过知了;我种过扁豆,种过丝瓜,种过南瓜,种过蕃茄。我觉得对自然,包括对动物和植物的亲近,是儿童教育很宝贵的资源,甚至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1947年我报名参加高考。从选择的空间来看,当时还是比较大的,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报考心仪的学校。由于父母专注于生病住院的哥哥顾不上我,都是我一个人复习、自己报名。后来我被金陵女子大学录取,就到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有一种比较好的校园文化,那种安安静静的氛围,我觉得很重要。
我在大学时代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能够容纳多元文化,我也能和各种各样的朋友交往。当时我们的校训叫“厚生”,就是“丰盛的生命”。我开始进入大学的时候是在化学系,也是出于科学救国的想法。后来学了一年化学,觉得人文的东西更适合我,我就转到了社会系的儿童福利专业。转专业的事情,父亲也很支持,还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大学生活的后期经历了战争,也经受了病痛的折磨,记得当时对我触动比较大的一本书是贝多芬的传记,贝多芬的那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它使我能够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对待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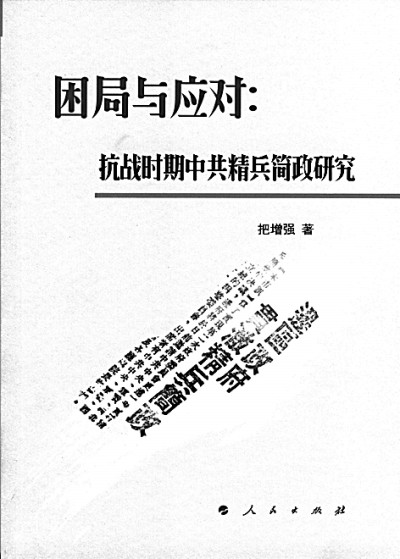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