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更多 |
有学问有情趣的人都是好人
——写在汪曾祺诞辰94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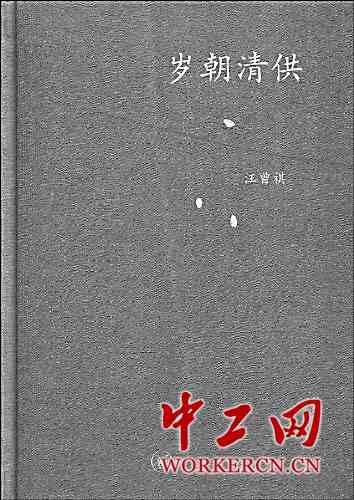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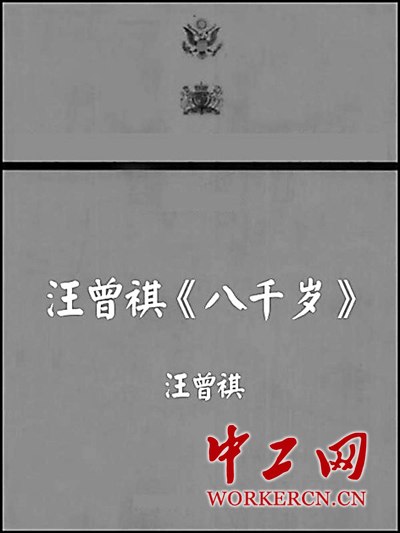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诗意的作家,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经历过乱世求学,经历过建国盛世,也经历过十年浩劫,他的经历如此纷繁复杂,但他笔下的文字却疏朗自然,云淡天清。他笔下有家乡明丽如画的风光,也有淳朴无羁的人情,还有世事无常的艰辛,但这一切,就像缓缓流过的水一样,湿了土地,太阳将它晒干,留下了淡淡的水印,拂去表面的忧伤,他的文字有滋有味,情趣盎然。
浸透纸背的文人情怀
汪曾祺的小说像是散文一般,语言飘逸而有诗情,像是江南清凉凉的风,又像是水乡湿润润的雾霭,在他湿润润、水淋淋的叙述里,独有一份安适的情致,浸透着传统文化的情怀。他写恬淡怡然的情节,也写苦难生活中的故事,写乡下的淳朴少年,也写过身带一官半职的人物,但是他们身上都有着挥之不去的传统情趣和文人情怀。
汪曾祺小说中的情趣,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人:《岁寒三友》里的画师靳彝甫,全家半饥半饱,还要种几竿玉屏箫竹,夏季在荷叶下养小鱼,冬日养几头单瓣水仙,家藏《秋虫谱》,用祖父留下的泥罐养蟋蟀,三方田黄石章,他爱若性命,在钧窑平盘里还养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
这样的上水石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出现了不止一次。在《寂寞和温暖》里,有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的桌子是这样布置的:“两本《古文观止》、一套《唐诗别裁》、一函装在蓝布套里的影印的《楚辞集注》……一个深深的紫红砂盆,里面养着一块拳头大的上水石,盖着毛茸茸的一层厚厚的绿苔,长出一棵一点点大,只有七八个叶子的虎耳草。紫红的盆,碧绿的苔,墨蓝色的虎耳草的圆叶,淡白的叶纹。”他的墙上挂着一把剑,这是一件真正的古代兵器,“鲨鱼皮的剑鞘,剑柄和吞口都镂着细花”。爱书爱诗,爱剑爱石,爱草木虫鱼,文人的不俗情趣已经在精致的生活场景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在旧式家庭的熏染中成长
汪曾祺的小说中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文人情结,这与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城镇的旧式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作为由本省学政选拔出的文行兼优的生源,贡入京师。据汪曾祺回忆,他的祖父就喜欢喝了酒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背唐诗,这倜傥的风度无疑在汪曾祺心中树立了最初的文人印象。汪曾祺的父亲则金石书画皆通,笙箫管笛俱会,尤其拉得一手好胡琴,他还有一间画室,每逢天气晴和,就会作画。父亲对他影响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不过他的父亲生性随意疏懒,也算是沾染了一点典型的文人“习气”,汪曾祺十几岁时,就与父亲对坐饮酒、抽烟,他父亲的说法是:“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而这种随性的文人脾气不但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还影响了汪曾祺的写作风格。
正是这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旧式家庭环境,培养了汪曾祺对于文人雅士情趣的审美,使他的作品常常带有浓厚的古雅趣味:画一张画就要喝二斤花雕的季匋民,作画舒展飘逸,意态像极了谪仙人李太白;一家四口人住在九平方米的房间,高大头还要在屋中悬四盆崖菊,面对批斗他一笑而过,决不耿耿于怀,交代材料字面上不硬顶,而在事实上寸步不让,这和与世无争的高人隐士并无区别;陶生风姿洒落,俊逸不羁,爱菊嗜酒,正是陶渊明的翻版……
所以,在汪曾祺这里,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好人”。他说钓鱼的医生王淡人有点傻,冒着生命危险泅水救人,换来一块“急公好义”的匾,为人们所鄙视的败家子治病,管吃管喝管抽鸦片,只因为“不给他治,他会死的”。他笔下的靳彝甫卖了心爱的田黄石章接济朋友,毫不犹豫。而有一位所长不仅虚心求教下级,还体贴关心同事,亲切之至,而且,他最不像所长的地方恐怕还是他在墙上挂剑、桌上摆石。总之,有学问有情趣的人都是好人,这仿佛成为汪曾祺不可打破的逻辑。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汪曾祺的小说中并不是只有恬美没有哀伤,而是作者用他温情的文字抚平了哀伤。《受戒》是汪曾祺最著名的作品,1980年10月,《受戒》的发表令全国文坛为之轰动。这篇小说与上世纪50~70年代小说的讲故事手法完全不同,情节淡薄却充满情味,小说中的人物率性自然,淳朴清雅,明海与小英子之间若有若无的感情让人沉醉,虽也蕴藏着一缕缕可以察觉的苦涩,但仍如身处桃源般恬静温馨。读者感受到了些许伤感和些许遗憾,但同时,最让读者感动的,却是在哀伤之余,隐藏在汪曾祺文字之下的人性天然之美。
汪曾祺乐于表现“美”与“健康的人性”。在小说中,他也时常表现出对那些富有情趣的生命的忧虑,但是这种忧虑,最终都被“美”抚平。在《天鹅之死》中,虽然白蕤被工宣队员折磨,左腿受伤,一到阴天就隐隐发痛,但是在作者眼中,“她还是那样美”。同样以“文革”为背景的《皮凤三楦房子》中的两个主人公也经受了游街批斗的苦难,但是他们生性豁达,好养菊花,很有些名士气度,汪曾祺还用调侃的语气说:“中国有不少人的友谊是在一同挨斗中结成的,这可称为‘文革’佳话。”幽默中略有反感之情,但是没有愤怒,因为愤怒早已被豁达消解,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这样的审美倾向就使汪曾祺的小说中弥漫着浪漫的悲悯情怀,汪曾祺自己也说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里所谓的“人道主义”,表现在小说中,正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古雅之士的情趣与文人急公好义、急人之急的品性正是悲悯情怀的真实写照。在文化与道德的对应中,汪曾祺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深深的留恋。他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中,他的文字就像清凉的风,安抚着一颗颗无处安放的躁动的心。(王彤)
参考书目
《汪曾祺小说》,汪曾祺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异秉汪曾祺人生小说选》,汪曾祺著,魏峨编选,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