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更多 |
有人说母校是那种自己狂喷乱骂可以,外人指手画脚绝不可以的学园。道理不错,不过我更喜欢“外人”责难母校,自己谩骂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况且学无所成,要骂难免暴露出内心深处残疾的心态。
伴着这个深邃的说法,花开花落之间稀里糊涂地就过了很多年,虽然待在北京,但关涉10年、20年之类的各种同学返校活动我几乎没参加过,唯一被照相的一次聚会也忘记了是因为什么项目。
9月末有同学电话说30年了,还是来吧,这次不少外地的同学都要来。想着咱也没埋怨过母校,再有同城、异地多年不见的同学可以认个脸,印证一下残存的记忆,于是乎,高高兴兴地又走进了标着“中国人民大学”字样的围墙。
不知道是否因为心情的关系,前些日子还在学校食堂吃过几次饭的我竟然发现了母校的变化:一些脸熟的楼宇新添了廊柱,外墙还多了可能有装饰作用的片状物,看起来美观不少,但这些花钱的物件不知道是不是有实用价值,似乎风格在变化的样子。记得当年读书的时候不是如此,彼时在俺宿舍北面新建了一处水泥柱的藤花廊架,虽然荣膺高校最差建筑十杰,但我觉得不错:起码不会让学子想到古代名人的葡萄架,结果人家说是基于实用。
脑子里这些杂烩画面有些让我惭愧。本来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幸运的时光,不仅是因为那个文化激荡、思想开放的年代,还因为良师的教诲:多位讲台上曾经的先生后来光彩四溢,成为国内教派的顶级好手,比如郑杭生,比如刘大椿……身披名校终生教授斗篷的班主任老师李德顺,昔时也是刚刚完成研究生学业。
可叹我不学无术,别说那些一级教授们当年风华正茂的风采逸事,就连先生们当面所讲,留下的记忆也很是有限。现在回想起来,印象较深的是班中女生稀疏,而且光彩也不怎么照人。这要怪罪于那时候的考试制度,除非决心在学习中寄托自己对容貌的哀思,否则女生决然考不过男生。不知道是男同学变傻了还是试题出了问题,想到现在名校也是美女如云,愚笨如我者好生羡慕。
收回遐思,待到同学围坐,才意识到感觉有异。知根知底的旧话不表,耳边响着老同学参与国家方略、治理统辖都市什么的高见,屌丝级别的俺听不明白,轮到列国巡游的帅哥说起黑人绸缎般细腻丝滑的皮肤,我的双眼顿时睁大了——但看的却是圆桌对面的女同学。
和关于30年前的想象完全不同,原来她们都很美丽。要说呢,长相基本上没太大变化,是我的审美变迁吗?可能,年轻时代理想误人,等过了知命之年理想破灭,才发现女人都很漂亮。可想想也不对,那时候只识皮囊,焉知女人之味?这样深刻的问题自己是解答不了啦,要是有阿平的判断力就好了,他凭借魏同学讲话的声调就科学识读出她已经是教徒。
可惜我不成,我只能用老花了的眼光在女同学那边扫来扫去,所想问题的深奥,也不过是不再年轻的某人会不会白发染色了。细致的观察之下还是有所发现:李教授变白了。虽然她性感的丰腴、安静和昔日一样,但记忆里她是有点黑的,现在看起来好像却比其他女同学都白:顺着肩膀下来,手臂也白。应该不是化妆的结果?又似乎还是化了妆:唇线明显。或许她本来就是那样,是我眼花和思维老化之故,抑或是受迈克尔(M.J)牛奶胡萝卜传说的启发,真的变白了。
话说回来,爱美,加上老同学的情谊,化妆才该是常态吧。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希望自己容颜常驻,美化自身和环境是美好的。然而这么美好的东西我却不太能够欣赏,大概是被“傻瓜吉姆佩尔”他爹辛格影响了,经常是一看到光亮得没有皮肤起伏的脸,如那些演员,我就会想到辛格说的话:在寒冷的列车里,那些刷了油漆的脸皮会像干裂的墙皮那样裂缝、剥落。
到了我的发言时间。一无所成的我还是老样子,“我喜欢黄家驹的歌词‘一生放纵爱自由’”。一句既能安慰自己又可以在同学面前不失面子的话,可我本来是想说:我不喜欢校园里那些新修的廊柱。际遇名师依旧没能被点化的我,相信大脑的优化还得靠内部存储,所以特别想对女同学说,我不喜欢化妆,我喜欢岁月留在脸上的痕迹,就像当初刚进校园时看见灰楼时的感觉那样。
但我没说出口,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老花眼没有信心,也可能是太多的遮蔽粉饰确实让人没兴趣再去说了吧。
| 红网:“大名陋室”诠释了以民为本 2009-11-24 |
| 人民日报海外版:迪拜危机的三点启示 2009-12-02 |
| 何 勇:内心温暖 所以富足 2010-09-27 |
| 人民日报:院士“特权”不宜异化 2009-12-07 |
| 陈滟莹:诗城马鞍山 2013-01-22 |
| 人民日报:院士“特权”不宜异化 2009-12-07 |
| 南京日报:别用“物质秤砣”衡量“古诗重量” 2014-10-24 |
| 光明日报:“大名陋室”诠释了以民为本 2009-11-29 |
| 趣谈文人书斋 2015-05-14 |
| 光明日报:“大名陋室”诠释了以民为本 2009-11-2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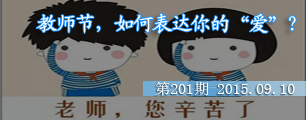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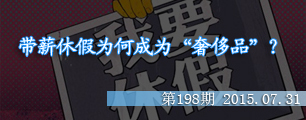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