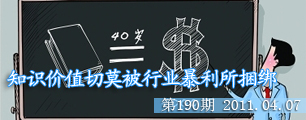| 分享到: | 更多 |
近日,“两高”联同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用四部门的话说,该《意见》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最大限度的司法关怀与呵护,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架起一道不容触碰和逾越的“高压线”。它既是向性侵不法犯罪分子果断亮剑,也是为未成年人撑起一顶坚实的法律保护伞,以帮助那些受伤的花朵早日走出阴霾,重新拥有美好的生活。
然而,法律规范尤其是刑法规范,绝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在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过程中,面对日趋严峻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惩罚犯罪分子仅仅是手段,防范犯罪分子及他人再犯罪,有效治理社会,实现社会的平和安宁才是最终目的。要真正达致此目的,就有必要处理好 “体”与“用”的关系。
就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而言,“体”与“用”的关系可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层面,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需要法律发挥主要或第一作用,这也是“法治中国”的题中之义。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规范尤其是刑法规范的功效当然要通过惩罚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犯罪分子来显现,但大多时候,法律规范尤其是刑法规范的功效是 “隐而不发”的,它的功效和威慑力主要是源自社会公众的“集体记忆”与内心认同。同时,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还要依靠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来辅助和配合。例如,防范“校园性侵”犯罪,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就必不可少。以道德规范、伦理规范等为代表的其他社会规范,尽管在防范犯罪、治理社会的功效上与法律规范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的功效更多地体现在“事前预防”上。换言之,要真正实现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法律规范之“体”,必须借助其他社会规范之“用”才能真正发挥其功效。
第二层面,在一个社会中,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数量与违法行为的数量相比毕竟是少数。从立法层面看,如果其他法律规范能有效地规制、惩罚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违法行为,刑法将无所作为。可见,要真正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在立法上,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规范才是“体”,而刑法规范则是“用”。当然这仅仅是从立法层面得出的结论,在司法层面看,我们在惩罚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行为时则仍应坚持刑事优先的原则,即如果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行为符合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必须严格按规定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如果不符合,则采用民事或者行政方式加以处罚。
第三层面,狭义的刑法仅仅是指刑法典,它主要由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组成。因此,在刑法典内部,“体”与“用”的关系则体现为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的关系。司法解释仅仅是对刑法条文的阐释和说明,它只能拓展刑法条文,绝不能脱逸刑法条文。该《意见》颁布尽管有利于法律的准确适用,增强了法律的应用性与可操作性。但是在认定罪与非罪、区分此罪与彼罪时,绝不能撇开刑法条文。例如,对《意见》19条中“明知”的认定,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该《意见》的规定。要正确认定《意见》中的“明知”,当然要结合刑法分则相关条文中关于“明知”的认定要求,而且还应注意与刑法总则条文中关于“明知”认定要求的区别。所以,为了准确认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效惩治并防范此类案件,就需要刑法条文真正发挥“体”的作用,该《意见》及其他司法解释绝不能以“用”代“体”。
诚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清末法学家沈家本也曾言:“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如果国家制定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执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将形同虚设,变成一纸具文,失去其应有的效力和权威。总之,《意见》的颁布固然可喜,但其生命力与公信力最终要体现为司法实践中的严格执行、有罪必罚。这不仅是防范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