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更多 |
在塌方式、系统性腐败频发的背景下,“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成了从严治党和反腐的发力点。各种建山头、拉帮派的行为,开始被反腐舆论一一清算,最新被点名的是干部“同乡会”。
21日上午,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在中纪委官网访谈中,直言“同乡会”不合“规矩”,“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就是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苏静称,有些干部聚在一起搞同乡会、同学会,看似漫无目的,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
新华社前不久点名“山西帮”的报道,则为这种一般性的批评提供了具体解读——“山西籍官员落马者中,令计划引发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根据其工作履历显示,令计划曾在山西工作了7年。今年6月19日,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其兄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报道还称,以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为核心,在此之前相继落马的一些中央部委官员,也因为祖籍山西或者在山西工作而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等都在其列。
当然不止“山西帮”。这种人脉拓展模式和交往特征,普遍存在于官场的“同乡会”里。除了利益输送、资源交换这些官场朋友圈的一般特征,以籍贯为组建基础的“同乡会”又别有特点。
“同乡会”因为带有乡情色彩,有能力在纯粹的利益交换之外构筑一条“情感纽带”。这使得本来松散的人脉圈子,更容易发展成为朋党。此外,“同乡会”以籍贯为基础,定义宽泛,常常由纯粹的官员朋友圈扩展成为官商一体甚至囊括三教九流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尤其容易成为权钱勾兑的平台。
此前,@人民日报评论就曾指出,“对某些干部而言,入团伙意味着进圈子,进圈子意味着进班子,团伙就是某些官员上位晋级的踏脚石;对某些商人而言,团伙意味着保护伞,既是输送利益的渠道,又是利益产出的‘聚宝盆’,商人就成了团伙圈子里的‘润滑剂’。既是一伙人,同操一摊事”。
更重要的是,“同乡会”是一种横向联合,其中显赫的圈子,能够横跨经济社会发展的几大关键领域,几乎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传统的腐败窝案只能调动本系统内的资源,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也往往比较集中——陈良宇与上海社保风暴、郑筱萸与药品审批乱象,都可以进行相对单纯的匹配和归纳。而同乡会式的圈子一旦达到“山西帮”这样的档次,却有联合操控诸多社会关键领域的能力,既可以彼此搭桥、共同拱卫,又可以各自为战、互相补漏,集团化的腐败由此产生。
当然,这是官场“同乡会”发展的极致状态。大多数这样的朋友圈,都处在一种打擦边球的状态。他们的日常交往并非有明显的利益互换、权钱交易,甚至没有具体的目标所指,而仅仅是为站队、示好、表态、情感投资、宣示服从内部规则、寻找到群体成员间的认同感,在交流、互动、冲突中形成了一个群体的交往规则和行为模式。换句话说,是一种腐败的准备状态。
不只同乡会,所有用籍贯、姓氏、师从、履历来组建的官场圈子,所有彼此勾肩搭背的官场“同年”“同门”“同乡”,大体都展现了这个趋势:建立纽带、形成文化、联合资源、预备腐败。两个月以来,中央对“团团伙伙”的再三警告,也因此有了明显的现实针对性。
同乡会被中纪委“点名”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评论《维护团结不许拉帮结派》,再次严厉批评“团团伙伙”。“一些干部就成了整天忙着寻找‘乡缘’‘学缘’‘业缘’的‘团员’。或是官官相护,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或是以同乡会、同学会为名义,暗中相互提携、互通款曲……派系意识流风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门户、不知有组织,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义。干部选拔,不问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决策论证,不凭实情民意,只看上边喜好。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将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对政治生态的危害之大,对政治规矩的破坏之深,对同志关系的异化之大,莫此为甚。”
结合“山西帮”的崩溃,由最高党报发出的评论不断敲打着寻帮拉派的干部们,站队要小心、点赞需谨慎。网罗人脉、构造阡陌交通的关系网曾被看作一种从政能力,交换资源、互相垫步也是一些官员的立身之道;现在看,成败皆萧何,官员俱乐部也可能一朝之间成为腐败集团。圈子越来越不好混了,不如花些时间重新检讨下,什么才是为官之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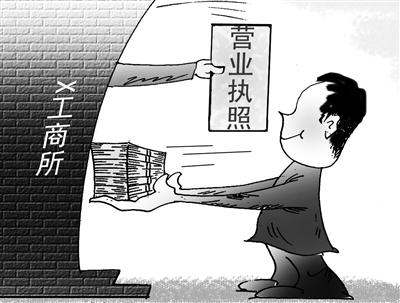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