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的第十个年头。在百年未遇的大疫情和中东国家内部发展危机、地区地缘政治危机冲击下,中东地区经历了危机重重的一年。一方面,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未缓解中东地区固有的冲突与对抗,内战、地区冲突、地缘政治博弈等危机事态持续恶化;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和加剧了中东多国本就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推高了中东国家的内部风险和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

1月7日,在伊朗克尔曼市,人们参加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葬礼。新华社发

6月30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一家医疗中心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3人死亡、6人受伤。图为一名女士在德黑兰关注爆炸现场的情况。新华社发

6月16日,也门首都萨那遭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多次空袭。图为萨那居民在屋顶望着空袭后升起的浓烟。新华社发

8月2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塞勒菲特附近的基夫勒哈里斯,参加抗议活动的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士兵、边境警察冲突。新华社发
“美难退、俄难进”
地区格局另类重组
2020年的中东地区呈现出更加混乱无序的局面,并突出表现为大国关系持续紊乱、地区力量发生另类重组、热点问题僵持且更加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联动等复杂局面。
首先是大国关系的持续紊乱。近年来,“美退俄进”成为学界对中东大国博弈特点的基本概括,但2020年却呈现出“美难退、俄难进”的复杂局面,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态势呈现“美退而不弱、俄进而不强”的态势,“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仍将持续很长时间。俄美进退乏力的状况使双方在中东的博弈以及它们各自与中东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进而使美俄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并导致叙利亚乱局久拖不决等问题。
其次是地区力量发生另类重组。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集民族、教派、地区主导权争夺于一体的对抗不断固化,双方的对抗呈现教派化、阵营化、代理人化的特点。在2020年,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的诉求与阿拉伯世界持续动荡分化、美国极力撮合、以色列四面出击等因素相结合,导致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在搁置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导致巴以问题很难再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将更趋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剧。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越走越近,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将继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此外,沙特和土耳其的竞争和对抗也不断激化,并日益围绕双方形成“亲穆兄会力量”和“反穆兄会力量”两大阵营的对抗,这一矛盾在2020年持续加剧,并构成双方在埃及、利比亚乃至西亚北非地区进行争夺的矛盾主线。
再次是热点问题持续僵持且更加复杂。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重启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军和伊核科学家遭“定点清除”,多处重要设施连续发生爆炸等一系列事件,都令伊朗陷入更深困境,伊朗在进行有限报复的同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美国也避免对伊发动大规模战争,但伊朗问题复杂化突出表现在伊核协议严重倒退、伊朗国内更趋保守化等问题上。在伊拉克,受2019年民众抗议浪潮以及2020年年初美国与伊朗以伊拉克为战场进行对抗的影响,在伊拉克前总理迈赫迪辞职后出现政府难产的困局,直至2020年5月才产生卡迪米任总理的新政府,疫情冲击、宗派冲突、极端势力复燃等使得伊拉克形势异常严峻。在也门,原有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对抗的格局下,原本与政府合作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与哈迪政府长期打击胡塞武装未果的情况下,开始于2020年4月自立门户谋求南方七省“自治”,并与政府军爆发冲突,这不仅使也门危机更加复杂,也使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加严重,抗击疫情更加困难。
最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联动。在中东地区,原有的内战或准内战、国际冲突等传统安全危机持续加剧,且新的风险源不断增加(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间的纳卡冲突以及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国家的强势介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核扩散、难民、海洋权益争端(尤其是东地中海)、水资源争夺(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等尼罗河上游国家)持续加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利比亚问题与东地中海地区海洋权益争端的联动。土耳其借出兵利比亚支持西部“民族团结政府”对抗东部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东部国民代表大会之机,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东地中海海洋划界协定。这不仅与埃及、希腊等七国组成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产生矛盾,尤其是导致土耳其与希腊的冲突加剧,土耳其还与支持利比亚东部力量的沙特、埃及、阿联酋、俄罗斯、法国等发生对抗。因此,利比亚冲突与东地中海海洋权益争端的联动使东地中海地区成为中东地区又一典型的动荡源,其背后的力量和矛盾盘根错节、异常复杂。
“阿拉伯之春”十年
回首犹叹转型难
“阿拉伯之春”爆发十年来,探索转型道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构成了中东国家的核心任务,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使中东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就人口规模而言,中东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病规模较高的地区。伊朗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17万;土耳其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6万。疫情使状况不佳的地区经济雪上加霜,能源、航运、旅游、会展等支柱产业遭受重创。据报道,2020年中东地区国家GDP将平均萎缩5.7%,战乱国家降幅最高可达13%。
当前,根据危机程度的不同,中东国家大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在2020年均在原有问题和疫情冲击下,陷入程度不等的危机,或面临不同程度的内部挑战。
第一类是受“阿拉伯之春”和长期外部干预影响陷入严重冲突动荡的国家,主要包括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它们持续处于内战、准内战或恐怖暴力泛滥、部落和族群冲突频发的状态,这些国家也是当前主要中东热点问题的当事国,它们面临战后重建、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的多重任务。
在2020年,叙利亚伊德利卜冲突频发,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叙展开复杂博弈;原本与哈迪政府共同对抗胡塞武装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与政府反目,使也门的冲突更加复杂;利比亚东西两部分在外部干预下陷入更加复杂的拉锯战;伊拉克政府缺位数月之久才产生新政府。因此,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对抗和冲突与外部干预相结合,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效应,使其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危机。
第二类是2019年下半年以来受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主要是苏丹、阿尔及利亚,以及受多重叠加危机(如政府难产、民众抗议、贝鲁特港大爆炸)冲击的黎巴嫩。发生政权更迭的阿尔及利亚、苏丹仍处在艰难的政治过渡进程之中;继去年下半年因民生危机发生民众抗议浪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今年8月又发生特大爆炸,充分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欠缺,在政府集体辞职后多次出现的政府难产再现。
第三类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代表的进入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的国家,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依然远未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埃及和突尼斯也曾再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但基本处于可控状态。疫情所加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民生危机,仍使埃及、突尼斯作为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代表面临严峻挑战。
第四类是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主要包括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伊朗、土耳其等,甚至也包括国内政治极化较为严重的以色列。这些国家都面临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能源需求严重下降、以沙特为代表的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进行价格战等因素影响,油价自今年3月以来跳崖式下跌,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经济尤其是财政收支平衡产生灾难性影响。据报道,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石油收入将锐减27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GDP将平均下降7.1%。这对于正在推动“2030愿景”框架下经济社会改革的沙特王室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外,沙特曾于3月逮捕前王储纳伊夫等一批王室成员和高官,足见其内部斗争之严重;沙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甚至是受疫情所迫停止朝觐,都遭到国内保守势力的批评和阻挠。
受疫情大流行和国际制裁冲击的伊朗则更加困难。今年伊朗进行议会选举,保守派大获全胜,改革派严重受挫,鲁哈尼政府更加弱势。伊朗进行的货币改革和“抵抗经济”均收效有限,无法改变伊朗经济持续恶化的局面。此外,以色列继2019年两次大选后于今年举行第三次大选才使联合政府艰难产生。近日,由于联合政府预算案未能按期通过,议会自动解散,将于明年举行两年内的第四次议会选举,也表明其内政外交存在严重的问题。
总之,2020年的中东地区危机是国家治理危机与地区对抗冲突并存的双重危机。冲突动荡国家的民生凋敝、转型国家的发展之困、热点问题的僵持无解、地区格局的混乱无序,都凸显了2020年中东地区国家治理困境和地区冲突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复杂局面。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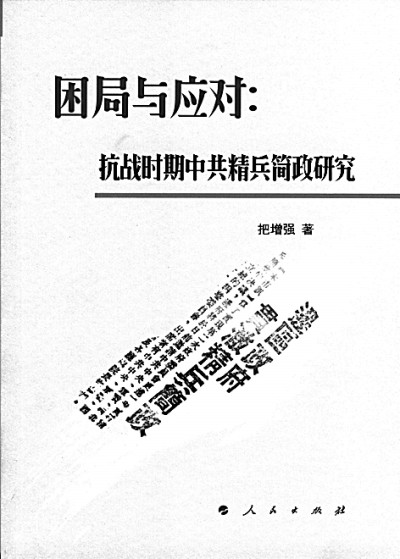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