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他乡·打工生活撷英】凌晨五点半
吊车和远树,黑黝黝地,一片模糊。仅在堤岸旁边,顺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才能看出一点轮廓来。帆布上堆满的棉袜,脚底下沙沙作响的落叶,还有口中隐隐哈出的白气,这些凌晨景象,让我想到寒冷的冬天。
煎饼、馄饨、粉丝,离两三百米就能闻见早点的味道。一辆小货车,匆匆开过来,搬下几笼包子,往折叠桌上一放,又匆匆开走了。吃早点的,都是附近的工人。没路灯,他们便把头灯打开;没凳子,他们便蹲在路牙上。他们从不说早点或早餐,习惯说早饭,而且饭量惊人,自带不锈钢的大碗,有的一转眼便是两三碗。
卖杂货的,除了用帆布铺出来的地摊,也有大包小包挂在摩托车车身上的,包里是手套、皮带和护膝,还有挤在三轮车车斗中的大桶小桶,桶内是瓦刀、卷尺和扳手。铺的、挂的,潮汐一般,随时能涨,随时能退。卖货的,大多中年人。一半是男人,他们受过伤,干不了重活;一半是女人,他们的男人,就在工地上。买货的,大多也是中年人,男人的比例高一些,女人也不在少数。这一卖一买之间,都用现金,他们觉得手握现金,踏实,愉悦。
工人们在凌晨时分的节奏是相当快的。他们必须很早起来,再困,再累,也得早起。他们必须马上吃饱,无论多烫,也得一口抢着一口咽下去。他们必须按时打卡,按时人脸识别,哪怕晚一小步,也得扣工钱。
跟他们一同醒来的,是自由鸣叫的飞鸟,一群群,在树林或星空中,扑棱着翅膀,互相追逐嬉闹。
个把小时以后,垂钓的,打太极的,才缓缓出门。那些垂钓的,盯着水面,一动不动。那些打太极的,虽然一直运动,但在工人们眼中,这蜗牛般的一招一式,要练出毛病来。
工地北边,有一条很长的河流。河面上,野鸭与黑水鸡,正悠闲地拨着水草。河面上,一排排杉树和柳树,一片片半枯半绿的莲叶,照镜子似的,朝自己的影子,看了又看。工人们每天早晚都要经过这条河流,却从没心思去看一眼倒影。河流东岸,有几棵高大的桂花树,打工的人们,什么金桂、银桂,才分辨不清呢。
凌晨五点半,水面上腾起的薄雾,把一阵阵凉意吹到了工地上。残缺的月亮,挂在吊车后头,它泻下来的清光,像冷霜一样,打得人周身发颤。工人们陆续就位,安全帽一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了。近旁的摊贩们,做早点的和卖杂货的,只用短短几分钟,便将战场打扫干净,一丁点纸屑都没留下。在这条逼仄的道路上,每天凌晨,都会准时准点地,上演一场市井大戏。
半空中,飞来了两只同样赶早的鸟儿,一只小白鹭,姿态优雅,还有只是灰喜鹊,好像落单了,到处乱撞。埋首干活的工人们,偶尔也会抬起头,用胳膊顶一顶帽檐,望望飞鸟划过的天空。
脚下的楼群快竣工了,建筑大军又将奔赴另一个工地。在那里,应该也有一条小路,也有凌晨五点半,也有风雨无阻的工人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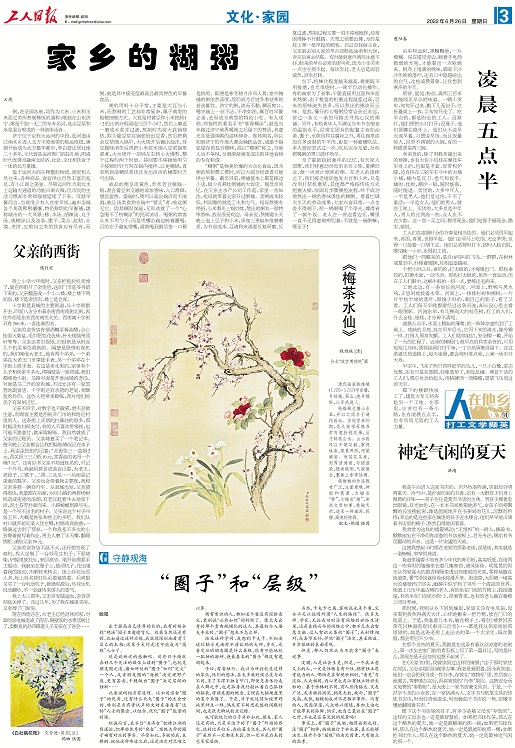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