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艾思奇在普及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贡献,是一般人不大了解的。
艾思奇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第二次留日考入了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他的本意是学习地质科学,发挥云南的资源优势,以推动实业救国为目标。这期间,他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然手不释卷,其刻苦精神为同学们所叹服。
艾思奇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搞哲学的人一定要懂得自然科学。他最早的职业是在上海泉漳中学任物理化学教师。做教师之余,艾思奇常为江苏省委的地下党报《日日新闻》写政治评论,还为“反帝大同盟”起草过宣言。他在上海时期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不仅是个人爱好,也是党组织领导的工作,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举办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写了许多科普文章。艾思奇发表了《谈死光》《谈潜水艇》《火箭》《斑马》《太阳黑点与人心》等一系列科学小品。其中,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内容最受欢迎。他还借自然科学文章抨击时弊,也令读者耳目一新。这期间,国际著名微生物科学家高士其脑部受到感染而患重病回国,艾思奇热情帮助他走上了科普创作的道路,他们成为一生的挚友。在延安时期,他又和徐特立、于光远、周建南等人组织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讲授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参与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大力倡导自然科学。艾思奇与发现北京猿人的人类学教授裴文中成为好友,他们和温济泽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工人们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社会发展史和自然辩证法,大力推动自然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小麦专家李振声曾提出,他自己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受到华罗庚和艾思奇的启发。艾思奇作为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做到了教学相长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反复强调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的新哲学。为此,他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宇宙线》两篇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为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做理论上的准备。1952年,艾思奇受马寅初校长聘请,在北京大学担任了5年的客座教授,重建了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他还“三进清华园”,为清华大学师生讲课,首次提出了“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论断,一时引起轰动。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应当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党校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党校编写了全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他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解决好哲学与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关系问题。1965年,艾思奇在《红旗》杂志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一文,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这篇反映哲学时代化的论文,是他逝世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坂田昌一也提出了“毛粒子”的观点,称赞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五)
艾思奇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良多,而且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传播同样注入了心血和热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邀请艾思奇讲课的需求量很大,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聘请他通过电台系统讲授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这样做,也开创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先河。 艾思奇对语言的学习有着天赋的能力。在日求学期间,他以超常的阅读速度和记忆力,吸收了广博的科学知识。为精确理解各国经典著作作者的本意,他在短时间内至少自学了日语、德语、英语和俄语,跨度之大难以想象。由于各国语言特点不同,经典著作的翻译版本文字也有所不同,他自创了多种字典连环对照的方法,准确印证了名家的思想脉络。看到祖父努力学习的热情和掌握语言的天赋能力,令我们这些后辈感到汗颜。他早年利用工作之余,翻译了海涅诗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从祖父的语言类学习笔记中看到,他到中晚年学习语言的劲头仍然不减当年,而且还更加勤奋。他上班前至少学习半小时外语。祖母王丹一跟我讲过,祖父一有功夫就扎进外文书店,购买自己喜欢的外文书籍和黑胶唱片进行收藏。他对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都要尽可能阅读原文。学习俄文时他格外精心,曾经收集了整箱的《斯大林讲演集》黑胶唱片。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艾思奇与学生之间启发式的教学关系。2010年,我去拜访大书法家欧阳中石老人。一见面,老人就和我说:艾思奇是我的老师。我开始还不太理解祖父怎么会是欧阳中石的老师,后来问了祖母王丹一我才知道,对中石老人来讲,艾思奇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上个世纪50年代初,欧阳中石先生考取了辅仁大学哲学系。一年后他又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中国逻辑史。当时,艾思奇正是北大哲学系的客座教授。
有一次上课之余,中石先生与艾思奇攀谈,艾思奇知道中石先生和齐白石先生熟识,就问中石先生知道齐白石先生画虾的事情吗?中石先生说知道,艾思奇说那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他画的虾是透明的。中石先生说齐先生画的是淡墨的,淡墨就透明,还画了许多虾的须,还有虾的腿,另外在虾头上的淡墨里面加了一点重墨。艾思奇继续问,就这样吗?中石先生说就这样,艾思奇说那你再看看去。中石先生带着艾思奇的问题,又来到了齐白石家看他画虾。齐先生在虾头部分先画一滩墨不很深,还往外洇一点,然后齐先生停下笔,又用一个小笔添很浓的墨,等上一会在这个黑墨里头再画了一道,很细很浓,经过这一道下去以后,这个虾就活了,就真成了透明的了。中石先生回来给艾思奇说,艾思奇说这回你看对了,他就是在浓墨中又有一笔焦墨。当时还很年轻的中石先生非常感叹,一个哲学家在观察一幅国画作品的时候,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太了不起了。
艾思奇的观察能力和认知能力确实不同于常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能够从画作中感受到齐白石先生的洞察力。他能够从虾头上的那很浓的墨,总结出“透明”与“混浊”的区别,说明他对齐白石先生画作观察之深入。他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齐白石先生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师的必然性。艾思奇通过齐白石先生画的虾,深刻地讲明了一点,那就是:一位深有文化底蕴的艺术家,他既要有整体认识,又要有具体的、局部的、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创造出常人所达不到的艺术高度。
今年也是我祖母王丹一诞辰100周年。她1937年11月去延安,比我祖父小整整10岁,他们1944年7月在延安结婚。之后,我祖母主要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工作。艾思奇去世后,她受邓颖超、李培之、郭明秋等同志嘱托整理艾思奇的遗稿。离休之后,她仍然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事业以及党校工作的发展。她依托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组织全国专家和开国老干部召开多次艾思奇纪念研讨会,出版了几十本论文集。她主持出版了《艾思奇文集》两卷本、560万字的《艾思奇全书》八卷本等一系列著作。1978年,她将艾思奇故居赠送给国家成立了艾思奇纪念馆。她和我讲过,艾思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我看到有些评论说,祖母王丹一把艾思奇的工作和贡献又延长了50年。
艾思奇是现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了解到的这些内容,只是只鳞片甲、吉光片羽,尽管如此也可以印证艾思奇内涵丰富的一生。他在我心中,是那么的立体,那么的鲜活。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的时代,艾思奇的哲学、自然科学、文学遗产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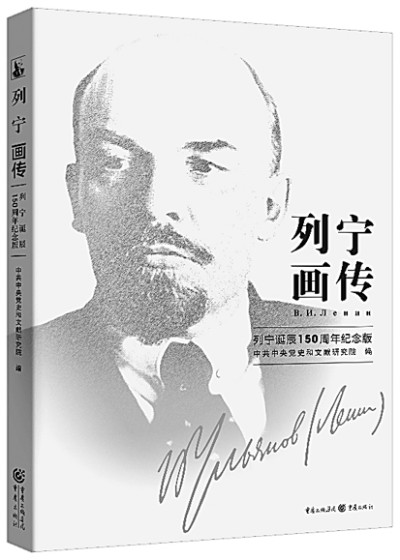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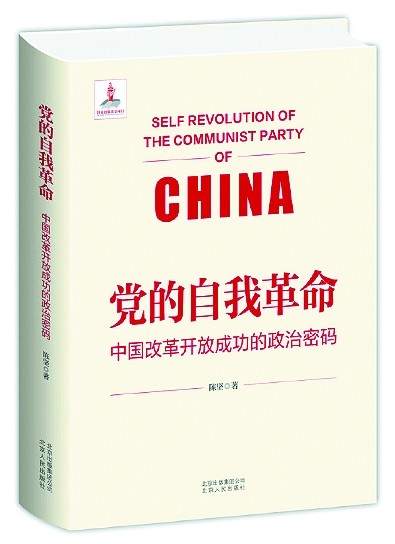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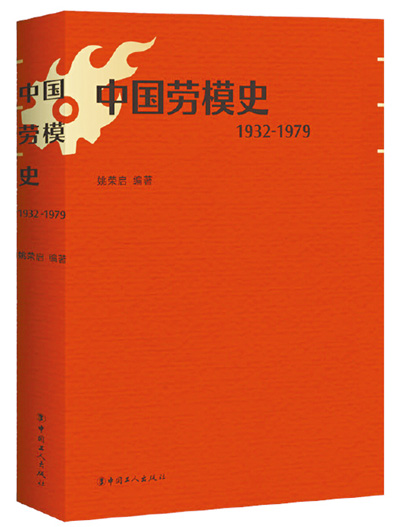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