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更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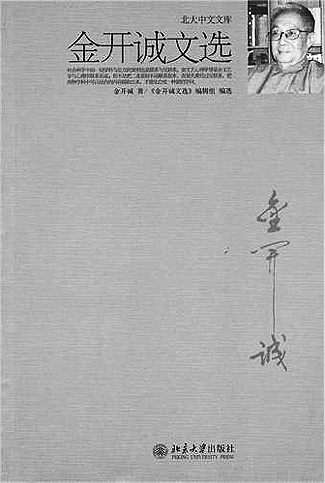
《金开诚文选》 金开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金开诚先生
1985年春天,我在欧阳中石先生处谈一部书稿,其间他突然问:“北大金开诚是什么人?”我知道他们认识,而且很熟,便说:“就是金申熊。”他说:“那太熟了,我们在京剧社……”欧阳先生是1950级哲学系学生,金公是1951级中文系的,他们都爱好京剧。曾经听金公说起过他们学生时代京剧社的事情。1995年12月,有一个涉及书法的座谈会在北大举行,我是掐着钟点去的,到会场时,离开会只有几分钟,看见金公和欧阳先生正在交谈。他们是戏友,也是书友,多年未见,谈兴正浓。我只跟他们打了个招呼,没有参与,以免破坏他们的话趣。
1961年9月至1964年11月,我跟金公在北大教工宿舍19楼201号房间一起住了3年多。我们同年出生,我虚长他40天。1955年金公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生,后改做助教,相继参加科研及古代文学的资料收集和注释工作,由现代文学转为古代文学。我们同住一室时,他的日常工作是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而我只在1957年至1958年上过一年中文系的课,后来就在系里做行政工作,不关教学与科研。
金公写得一手好字,却自称“还算规矩”。1961年11月,中文系举办教工书法展,金公起初没想参与,经人动员,写了一幅。平时谈起,觉得他独钟颜体。我请他介绍颜体的特点,他略加思考,用“端庄、厚实、威严”6个字概括,随后加以解释。这跟他后来谈论书法的文章里引用刘熙载《书概》论颜体的“苍、雄、秀、深”相近,只是较为通俗。1977年,金公发表《颜真卿的书法》一文,专论颜体的艺术特点。
金公篆刻也具相当水平。我曾经请金公为我刻名章,而且提出只要3个字,不要“印”或“章”之类。未得应允,也没有解释,只说:“下回进城,给你找一个人刻吧。”他比较了几位刻家的样品,最后选定请琉璃厂萃文阁徐焕荣刻。徐先生刀法别具一格,特别讲究印面布局。金公和我满意,周围看到的人也都赞赏徐先生的布局和刀法。我体味金公不肯刻的原因:名章,乃刻字匠所为,难以施行艺术安排。
1961年开始,游国恩先生担任部编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第一主编,全力投入文学史的编撰,编纂“楚辞注疏长编”的经常性工作全由金公承担。金公曾经说起,“游先生一两句话,我就得一两个月。”意思是游先生有时候只是提个方向、想法,具体的都得金公摸索、查找、抄录直至完成,包括查寻线索。有时候拟出按语,供游先生参考。偶尔发现某一偏僻的书里有关《楚辞》的资料,金公回到寝室说起,欣喜之状,我至今留有记忆。《金开诚文选》“前言”转述金公致周建忠信的话:“我涉猎楚辞虽然较久,但主要是做助理工作,过去的一切成果都应属于游国恩先生。”他认为,游先生是《楚辞》研究名家,《长编》是游先生创意,自己只是做了应分的协助性的具体工作。
2004年春天,已经过世的倪其心先生的《校勘学大纲》将要再版。倪公是我和金公都很熟的朋友。我给金公写信请他写序,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他给我打电话说,考虑了好久,论朋友关系完全应该写,可从来不给别人的书写序,最后说:“你还是饶了我吧!”不为别人的书写序,这是谦虚的另一种表现,对于出了名的人来说,是难得的自守。金公出书之后送我的,钤有“申熊初学”印记。学问再大,把自己摆在初学者的位置上,体现的是不断进取精神。
开诚先生为“知识丛书”写的《诗经》于1963年2月出版。他接受这个题目后,白天照常要去游国恩先生家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写。没有多少天,七八万字,交稿了。后来听组稿人沈玉成先生说,《诗经》是“丛书”收到的第一部稿子。因为是中宣部布置的任务,出书也快。在我印象里,从动手写稿到出书,前后也就半年多时间。这本书署名“金开诚”,是他第一次用这个名字。“文革”以后以此名行世。其时开诚先生正值盛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的东西能够有保证出版,无不尽心尽才尽力尽责为之。
金公在学界似乎是先以“文艺心理学”的著述闻名。我对此完全是外行,只记得1963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谈“意境”的文章,这当与文艺心理学有关。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沈庸”,我问为什么用这两个字,他说是无锡话“申熊”的谐音。这一笔名或可补入《文选》的“学术年表”。
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系里为20位成就卓著的已故教授编辑“文选”,每种20万字左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金开诚文选》为其中之一。“金选”27万字,依次按文艺心理学、楚辞研究、传统文化研究、书法艺术研究、随笔杂谈五类编排,收文26篇。相对于开诚先生数百万字的著述,可谓精中选精了。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开诚先生的《楚辞讲话》,是两百多页的通俗读物,也宜记入著述年表。
《著述杂谈》一文中,金公提到他文章中的两次微小失误。但我记得还有一次称得上“失误”的事。电台播放无锡盲人音乐家阿炳(华彦钧)演奏的名曲《二泉映月》。金公以无锡人的身份质疑:“二泉岂能映月?”过了大半年,他从无锡探亲回来说:“岂不知二泉真能映月。”他到锡惠公园实地观察之后,订正了自己的说法。这当然与著述无关,附记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