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诗传笺》
(西汉)毛亨 传
(东汉)郑玄 笺
孔祥军 点校
中华书局

《诗经名物图解》中的“荠”资料图片
由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的《毛诗传笺》称得上是中国古典第一流名著了,可是长期以来没有一个通行的点校本,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中华书局出版的孔祥军点校本《毛诗传笺》,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典籍丛书”,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我和门生分工拜读了这个点校本两遍,明确感受到这是一部标点、校勘都过关的合格的整理本。
西汉初年经学大师鲁人毛亨为《诗经》作《故训传》于其家,以授赵人毛苌。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毛苌为博士。毛亨、毛苌传授的《诗经》称为“毛诗”,他们的注释称为《毛诗故训传》,与鲁、齐、韩三家《诗》并行于世。东汉时期《毛诗》盛行,经学家如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皆治《毛诗》。郑玄合《诗经》、毛传而为之作笺,成《毛诗传笺》,在后世传授最广,影响最大。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学者阐发《毛诗》和郑笺,但基本亡佚。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毛诗正义》都选择《毛诗传笺》为标准文本。唐代雕刻的《开成石经》虽然没有注,但经文却采用了《毛诗传笺》的“毛诗”文本。孔祥军选择《毛诗传笺》作为点校对象,是对《毛诗》经文和古注的一次系统性整理,具有重要意义。
孔祥军点校本以清代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仿元相台本《毛诗传笺》为底本(简称仿岳本),是恰当的选择。岳本翻自南宋廖莹中刊本。廖本以建安余仁仲刻本为主体,精加校雠,更至臻善。《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余仁仲本《九经》为善本。廖莹中氏以余仁仲本不免偶有误舛,遂合诸本参订,又圈句读,后来居上。廖本失传,岳本是根据廖本重刻的,也失传了,所幸乾隆末年武英殿据天禄琳琅藏岳本重刻了《相台五经》,使这个善本得以衍传。现存的宋代《毛诗传笺》版本中,主要有南宋巾箱本、两个纂图互注本。纂图本大约是以南宋余仁仲刊附释文本《毛诗》为基础,加上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等内容形成的。“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类经书,文本质量一向评价不高。宋刊巾箱本《毛诗故训传》,虽然是《毛诗传笺》存世最早的刻本,但也是坊刻,用字不规范,且脱讹衍漏较多。如《小戎》经文“小戎俴收,五楘梁辀”下,脱传文“小戎兵车也”五字,他本不脱。宋刊本还有南宋刘叔刚刻十行本《附释音毛诗注疏》,但也是讹误较多的福建坊刻本。如宋十行本《緜》经文“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下传文“狄人之所欲”,宋刊巾箱本同;纂图本二种、仿岳本作“狄人之所欲者”。从上下文来看,以有“者”字为长。又《緜》经文“陶复陶穴未有家室”下笺文“诸侯之臣称君曰公”,宋刊巾箱本同;纂图本二种、仿岳本“称君曰公”作“称其君曰公”。当以有“其”字为长。又《云汉》经文“趣马师氏,膳夫左右”下笺文“又无赏赐也”,宋刊巾箱本同;纂图本二种、仿岳本“又”作“人”。学界一般认为,宋十行本经注及释文部分来自宋余仁仲本,但是从异文情况看,以余仁仲本为基础而成的纂图本二种在某些文字上与仿岳本更近,而宋十行本经注更接近宋刊巾箱本。宋十行本经注部分的校勘质量并不高。宋十行本而下的元十行本、永乐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阮本,皆以宋十行本为祖本。因此,选择仿岳本为底本是谨慎的。
版本选择的办法自然非校勘不可,孔祥军在校勘方面用功甚勤。他以武英殿重刻岳本为底本,广泛搜集了唐开成石经本、宋刊巾箱本、宋刊白文本、日本静嘉堂藏旧抄本、纂图本二种、宋十行本,进行了通校。又以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淳祐十二年刻《毛诗要义》、宋刻《吕氏家塾读诗记》、宋刻递修本《经典释文》等作参校,是对《毛诗传笺》的一次全面校勘。在此基础上,对异文进行考定,如仿岳本《板》经文“昊天曰旦,及尔泳衍”下有笺文“人仰之皆与之明”,孔本改“与”为“谓”,并出校勘记云:“谓,原作‘与’,据诸本改。案:《要义》所引、《读诗记》所引并作‘谓’。”改动有充足的版本依据。在参校的版本当中,我们发现,孔本使用了宋本《毛诗要义》。这部《毛诗要义》当源自已经失传的越刊八行本,有较高的校勘价值。我们注意到孔祥军在完成《毛诗传笺》点校之前,曾撰文《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毛诗要义〉考异(郑风前部分)》(《域外汉籍研究》第十四辑》),就揭示《毛诗要义》当中的疏文较之宋十行本,多有胜处。《毛诗要义》所录经注,虽不及节录疏文那样丰富,亦弥足珍贵。参校《要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行本失传的遗憾。孔祥军的校本比较丰富,其中日本静嘉堂藏旧抄本、宋十行注疏本等,都是阮元未见到的。这对读者了解各本的异同,大有帮助。如《车舝》笺文“人皆庶几于王之变改”,孔本出校勘记云:“人,日抄本作‘心’,十行本作‘必’。”从书法角度考虑,人、心、必这三个字有内在关系。
孔本的标点断句相当谨慎。如《韩奕》经文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郑笺云:“汾王,厉王也。”孔本于经文“汾王”未加专名线,于笺文“汾王”下加专名线。原因是毛传云:“汾,大也。”是毛传释“汾”为“大”,而郑玄以为“汾王”是厉王,孔本于此处经文当中的“汾王”不加专名线,而郑笺当中的“汾王”却加专名线,从而体现出毛传、郑笺的不同。又如《鱼丽》传文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初读起来,似乎点作“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更为顺畅,然而孔颖达《正义》云:“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谓寒霜之劲,风暴又甚,草木枝折叶损,谓之折芟……定本‘芟’作‘操’。”据此,可知孔本的标点是根据孔颖达《正义》。从这些细微之处均可见标点的精当。这是全书在标点断句方面一以贯之的风格,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这个点校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个别地方也还可以再作斟酌。如《韩奕》笺文“以期先祖侯伯之事尽子之”,仿岳本同,然江南书局摹雕仿岳本改“子”作“予”。检宋刊巾箱本、宋十行本、日抄本作“予”,当以作“予”为是。又如《遵大路》:“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陆德明音义:“寁,市坎反。”仿岳本同,国图藏宋刻递修本《经典释文》亦同。黄焯《经典释文汇校》引宋毛居正《六经正误》云:“帀坎反,作‘市’误。”又引段玉裁云:“毛说是。”盖“帀”“市”形近之讹,当予指出。对全书来说,这只是白璧微瑕,希望重印时稍作修订。
(作者:杜泽逊,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张剑,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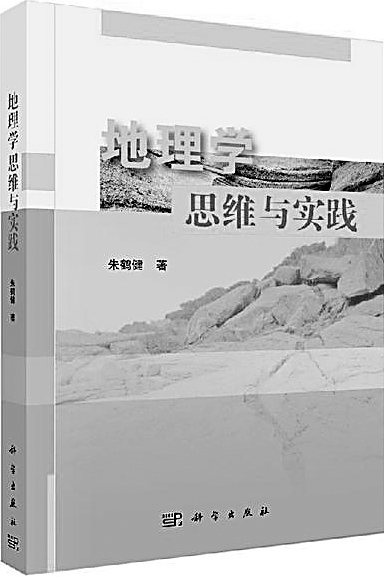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