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规范性陈述,犯罪论体系背后蕴含着对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刑罚目的、刑事政策等多重因素的深层考量。这种深层考量不仅来自于刑法体系,需要以刑法规定为中心而逻辑展开,而且涉及刑事政策、宪法等,需要把刑事政策意义上的需罚性、宪法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纳入其中,以使犯罪论体系更好地发挥人权保障的功能。
建构犯罪论体系旨在发现刑法公理或提供法律议论框架,使这种刑法公理指导司法官依据刑法进行司法裁判,依此可以确保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犯罪论体系必定是实践导向的,并以理论的自洽性与融贯性为依归,两者分别对应犯罪论体系的解释力与供给力。司法实践具有复杂性,进入司法实践中的案件,亦有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之分,对一般案件而言,犯罪论体系可以提供一般刑法公理,法律实践者按照犯罪论体系提供的入罪与出罪标准把握,就能正确理解法律并作出合法公正裁判。面对疑难案件,需要在犯罪论体系中植入一个法创造的法律议论框架,使法律议论以犯罪论体系为主轴展开。
作为一般刑法公理的犯罪论体系
法学家有关犯罪论体系的建构,整体上是法律公理体系之梦的体现,即通过对刑法体系、刑事政策、宪法等有关定罪的规律性、逻辑性与经验性的发现,建构一个涵盖入罪与出罪、事实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的基本教义,遵循这一基本教义,法官的司法裁判便有了指南。对一般案件而言,犯罪论体系作为公理体系具有逻辑推演上的正确性,追求的是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主客观性。犯罪论体系的本质是论证,它是一种事实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的综合体系,作为事实性陈述,犯罪论体系是以实定法为中心进行建构,不能是对未来法律的猜测,对司法实践中的定罪标准、定罪范围(共犯)、罪数等立足于实定法进行客观反映,需要把司法实践定罪的一般性要求予以规律性呈现,需要把全部刑法条文、全部重要性陈述纳入体系之中。作为规范性陈述,犯罪论体系背后蕴含着对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刑罚目的、刑事政策等多重因素的深层考量,这种深层考量不仅来自于刑法体系,需要以刑法规定为中心而逻辑展开,而且涉及刑事政策、宪法等,需要把刑事政策意义上的需罚性、宪法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纳入其中,以使犯罪论体系更好地发挥人权保障的功能。
犯罪论体系的主客观性以逻辑正确为前提,逻辑性是确保犯罪论体系具有解释力、供给力的前提,掌握了犯罪论体系的方法与标准,对一般案件而言,就可以确保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依据刑法、司法解释作出判断与法官依据犯罪论体系作出判断,是司法实践与理论主张的分野,犯罪论体系是法学家法而不是实定法,它提供的是司法官认识刑法、司法解释的理念、路径与方法,有了完善的犯罪论体系指导,司法官对刑法适用才不至于出现偏误,才可以实现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无缝对接。因此,犯罪论体系对司法实践具有定位功能、指引功能与修正功能。定位功能意味着犯罪论体系能够让裁判者迅速明确案件的争点在哪里,是因果关系问题,还是主观罪过问题;指引功能意味着引导裁判者按照什么顺位、方法去定义犯罪。比如,按照“先客观、后主观”和“先事实、后价值”的方法,以免出现主观定罪、先入为主。就此而言,犯罪论体系给司法官提供的是理念、思维与方法。修正功能意味着当依据刑法规定得出“合法但不合理”的裁判结论时,犯罪论体系的功能与刑法机能不同,刑法的正当性来自于惩恶扬善,满足民众的报应情感意味着不能放纵犯罪,犯罪论体系主要在于法官定罪提供一种过滤网,旨在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故当法官定罪出现“合法但不合理”的情况时,需要依据建立在“入罪合法、出罪合理”法理基础上的犯罪论体系予以修正。形象地说,犯罪论体系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健身房、正衣镜、消毒柜的功能。
犯罪论体系除兼顾一般案件外,还必须为疑难案件的公正裁判开辟理论通道,疑难案件意味着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裂缝,司法官在裁判中“依据法律”往往存在多种法律适用方案,如何在多种法律适用方案存在竞争时选择最优的法律适用方案,此时,犯罪论体系难以事前供给司法官可以直接适用的公理,而是需要为最优法律适用方案的出现提供法律议论框架。
作为法律议论框架的犯罪论体系
由于法律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且社会生活一直在概念,刑法规定与社会生活之间无法无缝对接的矛盾,造成疑难案件,典型如许霆案、二维码偷换案、于欢案等,在面对疑难案件之时,犯罪论体系为案件处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讨论提供了一个议论框架。
法律议论框架可以视为犯罪论体系的程序维度,面对疑难案件,司法官并不能拒绝审判,疑难案件的处理作为难点恰又体现着刑事司法的高度与温度。疑难案件形式上涉及司法官自由裁量权,实质上涉及案件处理之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小心求证。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国家,疑难案件之合法性与合理性交给陪审团来决定,同时也包含着对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信任与制约。在我国这样不实行陪审团的国家,把案件处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交给司法官自由裁量权并不可期,必定还需要借助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建构,来正确评判案件处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提供一个控辩审三方进行法律议论的框架与标准,以引导司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而不是相反。要特别强调的是,疑难案件本就意味着法律自身确定性不足,此时案件处理的合法性观点,必定是一种众说纷纭的格局,此时,追求案件处理的合理性,包括强化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恪守,应当是案件处理取得民众认同的关键。
作为法律议论框架的犯罪论体系,它的立足点在于刑法条文本身的不确定性,要解决的矛盾是不确定刑法与新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对应,这种对应无法追究主客观性,因为法律本身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对应,但是立法本身不能为个案而立法,且缓不济急,与此同时,法官面对这些案件时又不能拒绝审判,必须给此类案件一个裁判结论。犯罪论体系在面对这类案件时显然也不能提供一个依据犯罪论体系直接得出的结论,毕竟,学说不是刑法渊源。犯罪论体系此时能完成的任务是为案件处理提供一个法律议论的框架,如立足于“入罪强调合法,出罪强调合理”的法理,把需罚性纳入犯罪论体系判断。以许霆案为例,此案从个罪构成要件出发,定盗窃罪尚无疑问,但从需罚性出发,则会面临疑问,因为这是一个千年不遇的案件,处罚这样的犯罪人,既不能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也不能实现特殊预防目的,在如此框架下讨论许霆案,则为“出罪强调合理”开辟了一个议论框架,也意味着为案件的合理界分增加了更多考量要素。
在疑难案件中,法律议论是为解决“刑法适用选择两难”的争议而采用的司法审查技艺,是司法官因受刑法条文不明确规定制约、受刑法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裂缝约束,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所作出的更为理性的讨论。为何需要犯罪论体系提供一个议论框架,这是作为认知科学的犯罪论体系背离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无法涵盖作为规范实践的司法过程全貌,犯罪论体系是立足于“刑法是什么”的本体论认知,讨论“刑法应当是什么”的规范论解答,有一个实然到应然的转化,这种转化就会带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缝。犯罪论体系具有确立定罪标准、反映定罪过程、过滤不当入罪等方面的功能,但是它本身并不是法源,它只是给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提供了一个议论的基本框架,如不法的范围与程度,有责的判断标准等,有了这样的基本框架,控辩审三方的法庭论辩才不至于成为一种“没有底盘的游戏”。
疑难案件的裁判往往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效应,因为,在疑难案件中刑法适用或者裁判认同往往有困难,控辩审三方在犯罪论体系提供的议论框架下充分辩论无疑有助于降低错判风险,使裁判结论更具有合理性。对于此类案件裁判而言,法律议论与其说是追求真理,不如说是追求共识,与其说是确保合法性,不如说是确保合理性,犯罪论体系提供的不法与有责区分、入罪强调合法与出罪强调合理、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与超法规的违法责任事由、要罚性与需罚性等核心法教义学概念,都有利于揭示隐含在犯罪认定中的出罪逻辑,从而解密疑难案件的“论证规则”,避免从刑事政策的意义上去构建社会危害性、处罚的必要性与刑事裁判之间的简单推导关系。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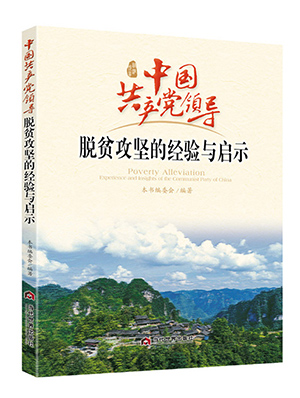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