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整体面貌及其概括,学界存在不小的分歧。日本学者曾以“律令法系”概括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一度在中国法律史学界广为流传。刘笃才先生提出“律例法体系”说,建议用“律例法体系”承接“律令法体系”,作为理解明清法律体系的基本概念。杨一凡、陈灵海先生提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说,认为会典乃明清王朝之大经大法,明清法律体系“以典为纲,以例为目”。学者吕丽提出“三大法律门类”“三大法典”说,提出传统法律体系可以划分为三大法律部门即律、行政法、礼仪法,与之相应亦存有三大法典即律典、行政法典、礼仪法典。俞荣根先生提出“礼法体制”说,认为传统法律体系是礼法体系,包括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马小红、武树臣提出“混合法”说,认为“混合法”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内在传统,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兼具大陆法系“制定法”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混合性特征。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其中是否存在“判例”“判例法”“民间法”?是成文法体系,还是“混合法”体系?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法史学界,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解答。
法典主体: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
法典是经过整理,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严格意义上的法典不应当包括法律法规汇编,而是立法机关制定并实施的某一法律部门集中系统的法律文件,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一致性等特征,是成文法的高级形态。纵观历史,法典绝非迟至近代才有,《汉谟拉比法典》《十二铜表法》《国法大全》等法典足可为证;放眼全球,法典也并非西方法律文化之专利,《唐律疏议》《大宝律令》足可为证;虽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享誉全球,但在法律史上享有盛誉、影响深远的并不只有民法典,早在“民法典情结”形成之前,古代中国以及周边诸国就产生了“唐律情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吉同钧:《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闫晓君整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
在“法典情结”下,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大体由法典、单行法、成例、法律解释所构成。法典主要包括律典、令典,还可能包括会典。单行法主要包括制诏、科、格、式、敕、条格、榜书、大诰、条例、则例等。成例指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经最高统治者认可和一定程序,具备可以援引作为处理类似事件和审理类似案件依据之效力的事例或案件,主要包括成、廷行事、比、法例、断例、事例等,可能还包括成案、故事。法律解释主要包括法律答问、经朝廷认可的私家注律、申明、看详等。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干,民间规约、习惯、情理、经义并非正式法律渊源,法律效力不确定,虽然有助于丰富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法律实践的认识,但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仍应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基于此,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体系,以法典为主体,法典居统率地位,统摄法律体系。律典“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翦乱除暴,禁人为非”,(《隋书·刑法志》)令典“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新唐书·刑法志》)会典“立纲陈迹之端,命官辅政之要,大经大猷,咸胪编载”。(《雍正会典》卷首,御制序,文海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单行法是法典的辅佐和具体化,成例是为补充法典的漏洞而存在,法律解释主要是对法典具体适用的解释。
“法典化”: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演进路径
“法典化”指一种大规模制定法典的趋势与过程。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法律大体经历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进过程,成文法产生后,法律形式的进化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向更高形态的法典转化,“成文法之初起,不过随时随事,制定为多数之单行法。及单行法发布既多,不得不撮而录之,于是所谓法典者见焉”。(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演进,是沿着“法典化”的路径而进行的。第一,“礼刑体系”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之肇始,是“法典化”之前夜。西周“礼刑体系”以礼和刑为法律体系之主要构成,习俗和成例是礼、刑的主要存在形态。第二,“律令体系”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之成型,是“法典化”的发端及正式开启时期。战国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帝国的划一治理需要、兵刑钱谷等行政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从“礼治”到“法治”治理模式的转换,皆使得成文法大量产生。同时,成文法体系化的内部动力、律学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提高,又使得“法典化”在魏晋之际于成文法体系内部兴起,最终促成了门类齐全、内容完备、体例严谨之律令法典的产生,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礼刑体系”过渡到“律令体系”。第三,“典例体系”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之成熟阶段,是“法典化”的升华时期。唐宋之际,格后敕、断例等单行法和成例地位上升,“律令体系”发生了重要的嬗变。元代“弃律令用格例”,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制定了律典、令典和会典等成文法典,逐渐发展起以条例、则例、事例为主的例的体系,形成了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成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体系”。
总之,“及春秋战国,而集合多数单行法,以编纂法典之事业,蚤已萌芽。后汉魏晋之交,法典之资料益富,而编纂之体裁亦益讲,有组织之大法典,先于世界万国而见其成立(罗马法典之编成在西历534年,当我梁武帝中大通六年。晋新律之颁布在晋武帝泰始四年,当彼268年)。唐宋明清,承流蹈轨,滋粲然矣。其所以能占四大法系之一,而粲然有声于世界者,盖有由也”。(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中国古代成文法产生于春秋时期,“法典化”则发端于秦汉时期,而正式开启于魏晋之际,促成了律典、令典等规范化法典之产生,缔造出隋唐帝国盛世与律令制国家,影响波及周边诸国,中华法系由此成型。自魏晋之际法典产生后,除元代等个别王朝外,绝大部分传统王朝都制定了法典,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成为以法典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
法典驱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法源变迁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法源变迁由法典变迁驱动,法典的变迁带动了法律体系中各种法律渊源的变迁。春秋战国之世,刑书公布标志着“以罪统刑”成文刑法开始产生,加速了制定法取得主导地位。礼、典、常、则等更多包含习惯和先例的法律形式出现了衰颓的趋势,誓、命、令、刑等法律形式越来越被改造成直接反映统治者意志的、有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的制定法,并在不断强化的现世权力的支持下,逐步取得主导地位。魏晋之际,“法典化”开启。三国曹魏《新律》首次真正具有了法典所独有之整体性、系统性和概括性,之后晋律以空前简约之面貌横空出世,更可谓一种系统化、整体性的成熟法典。晋令汇众令于一体,通过对令文的概括和抽象、对篇章内容的高度浓缩,以简约之令条,层层递进、紧密相连之篇章,承载和容纳国家基本制度,完成了令的法典化。律典和令典的制定带动了秦汉以来繁多芜杂的法律形式的简化,并导致对成例适用的严格限制。西晋刘颂为三公尚书,上书云:“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晋书·刑法志》)主张以律典来统一指导司法活动,反对成例的适用。《唐律疏议·断狱律》“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条规定判案具引律令为司法官员之明确义务,“辄引制敕断罪”条又规定制敕权断的案例不能自动生效,从而把成例的产生和适用限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内。
从唐后期开始,长期停止修订的律令法典已无法适应剧烈的社会变迁,格后敕地位上升,成例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开始增加。《开成格》规定大理寺和刑部可以“比附”断案,而且“比附”断案“堪为典则”者,可以“编为常式”,(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51页)赋予中央司法机关比附成例断案和编撰成例的权力。延至宋代,作为单行法的编敕成为宋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例的法律效力得到了成文法的认可和司法实践的支持,上升为正式的法律渊源,“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史·刑法一》)以法典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出现了“去法典化”的变迁趋势。元代“弃律令用格例”,律典和令典等法典被废弃,条格和断例成为元代法律体系的主要构成。汲取元代条格、断例过度膨胀导致法律适用混乱不一的教训,明清王朝重新制定法典:会典“大经大法”,载“经久常行之制”;律典逐渐与条例合编,名为“律例”;令典则有名无实,逐渐消失。延续元代法律体系“例化”之特点,明清法律体系继续接纳成例为正式法律渊源,同时尽可能对成例进行一定的概括和抽象,将其升华为具有某种一般性的条例和则例,更多地具备成文法的属性。
法典和“法典化”是法律史上的典型现象。法国大革命前,基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国王路易十四和法律家努力将分散的旧法律组合成统一规范的法律体,实为近代欧陆“法典化”之起源;19世纪,随着《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的产生,全球范围内第一波“法典化”浪潮在欧陆兴起,进而波及美国、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和地区; 20世纪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典编纂开启了第二波“法典化”浪潮,一些西欧国家修改或重新制定了各自的宪法典、民法典,中国、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开始制定民法典。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有国家制定新的法典或对其既有法典进行再编纂,全球范围内“法典化”虽然遭遇“解法典化”之挑战,却未停止其脚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过,不仅构成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之重要成就,亦可视为全球范围内“法典化”的又一重大进展。法典和“法典化”不仅构成中国法律史之悠久传统,亦成为世界法律史之普遍现象,其中必然包含丰富、深刻、生动之法理,需要进一步发掘与发展,如此,方可既得法典之“形”,更得法典之“意”。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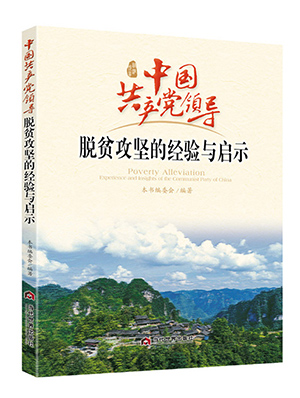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