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全球化的演变和中国的继续开放
张锋:任何人的思维都具有惯性,一个国家也是。在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上一旦形成了既定思维,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集体意志,这股力量对世界格局的重塑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几十年间,经济全球化在崇尚科学技术和经济理性的作用下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一进程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在过去这些年里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越发严重了,蓄积的社会情绪也越发高涨。如今在一些欧美国家出现的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潮流,就是这类情绪的一种表达。那么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是否也会随之退潮呢?
郑永年:这个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的判断是,经济全球化不会简单地退潮,而是以一种“有限全球化”的新形态继续下去,比如回到类似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全球化。那时的经济全球化是每个国家都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和投资。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优化配置。
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这种更为我们所熟悉的深层次经济全球化确实给部分国家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多还在进一步恶化之中,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是此轮经济全球化中最突出的受益者就否认这个事实。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占到70%,但是奥巴马执政结束的时候,勉强只有50%。经过此次疫情的冲击,这个比例还在下降。站在美国的角度,大量中产阶级滑落到社会中下层,甚至沦为贫困。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这个现象,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学界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已经有了共识,但知道成因并不意味着找到了解决办法。再加上多边政治的协调机制天然地效率低下,这就让一些国家和利益团体对此失去耐性,他们迫切地想要回到“昔日的美好时光”。在那些“昔日的美好时光”里,国家层面最不同的特点就是各个国家都还掌握着“经济主权”。20世纪80年代以前,技术和资本当然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但其程度和范围远不及今日。比如,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央行还不至于在货币政策上失去话语权,而这种失去在如今的欧洲国家相当明显。对于美国来说,那时候它的资本和技术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流动,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把供应链布局在全球,特别是集中于中国一个国家。
疫情将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缺点充分暴露出来。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发生后情况依然很惨烈,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使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产业链大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不仅缘于全国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有赖于医疗物资相对充分供给的经济优势。虽然中国刚开始医疗物资也曾短缺,但随着产能快速提升,供应很快基本缓解。因此,疫情之后各国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还是经济安全考虑,都会设法促成一些产业的回流,也就是要更多地把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经济全球化会因此转变为“有限全球化”。
张锋:有限全球化,较之过往的经济全球化,可谓是人类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中非常重大的变迁。如果有限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将来的局面会不会对中国非常不利?
郑永年:这需要分短期和长期来看。从短期看,这种局面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不利的,因为这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但也不用对这种冲击过于恐惧。在有限的全球化下,美国、日本等国家即使将企业迁回本国,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内完成。就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言,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他们的供应链网络优势明显,外资企业中的一部分即使要执意迁走,也还有一个必然的过渡期。
从长期看,不利的影响未必那么大,甚至可以预期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企业不可能全部撤离。有些领域例如汽车产业,西方企业在中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不可能把整个产业链撤出中国;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会让出原本由他们占据的中国国内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可以迅速代替他们占领这部分市场。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是可利用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以上积极预期离不开一个关键因素的支持,就是中国总体上仍旧保持开放,而不是走向封闭。由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一下中国会不会在疫情之后走向封闭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对中国继续保持开放,乃至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张锋:中国人历史上吃过“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亏,不应该对此缺乏认识。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已深入人心。新冠肺炎疫情固然凶猛,但比起历史上因为封闭带来的“痛”,比如改革开放前因为封闭带来的“穷”,是小得多的损失,中国怎么可能会重新走向封闭呢?
郑永年:中国正在尽可能防止出现“重新走向封闭”的结果。但基于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我们有必要对此有更加谨慎和明确的认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即使美国开始大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领导层也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多个场合表示决心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中国通过艰苦的努力和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都证明中国是有强烈意愿进一步开放的。但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看到,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了,尽管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体系,但突然间,人们发现西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
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互动关系,已经从以往“拉”和“推”,正朝向“挤”和“退”演变,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想把中国挤出世界体系,中国面临着是否“退”出这个体系的问题。“退”不是表现在物理和物质意义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态度上。
以中国的体量和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纵使外界有再多不利因素,中国也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走向衰落。不过,面对西方的“挤”,中国如何保持不“退”,是当今中国人需要认真面对的挑战。
如何从人类价值的高度反思疫情
张锋: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经济全球化,更不是所有人都乐见一场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以往在世界范围内累积的问题,借由这次疫情突然爆发出来,短期来看是对于过往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长期来看,很有可能重塑这些秩序,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有限全球化”和中国在其中是否能够继续扮演开放者的角色。这些问题,仅仅在半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不得不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意外值得人类社会从方方面面进行反思。郑教授,您觉得如果上升到人类价值的高度,我们该有哪些反思呢?
郑永年:这其实是一系列宏大的问题。
首先,我始终认为抗疫的核心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的关系,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在制度文化层面进行反思。制度文化是人类基本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也是争议极大的一部分。就制度而言,有几点是人们必须有所认识的:第一,每个国家的制度都是根据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发展而来,并且是向历史开放的,在不同阶段与时俱进,以应对变化。第二,制度具有可变性和灵活性。没有任何一个制度会像“民主论者”或“专制论者”那样刻板地存在和运作。任何制度都既有其民主的一面,也有其专制的一面。在应对危机的时候,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分权,分权的体制可以转向集权。第三,制度操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领导能力问题非常重要。制度是由人来操作的,同样一个制度由不同的人来操作,效果会很不相同。
其次,在公民与社会关系层面,每个公民都应该力图找到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交会点。社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疫情防控并非仅仅是医生、政府官员、志愿者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不管是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众多个体能否有效集合起来,决定了战疫的成败。结合上面提到的制度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但他们的“权”又都有其界限。每个人都有权行使他的自由,其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果妨碍别人的自由,社会有权制裁他。换句话说,个人自由的行使必须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利益。
最后,在超越国家和个人的国际层面,虽然西方国家最早提出了“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但这至少不是人性的全部。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任何国家和个人都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是疫情大暴发时期的需要,还是在任何时期检验人类道德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在人道主义领域有所作为,中国能够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展示其大国的责任担当,这非常符合中国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本期统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文字整理:张骏、李明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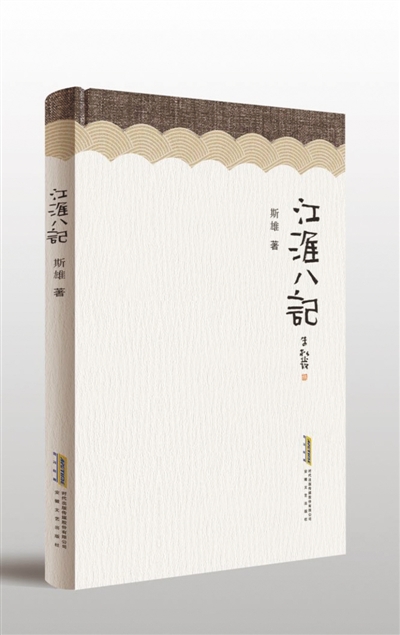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