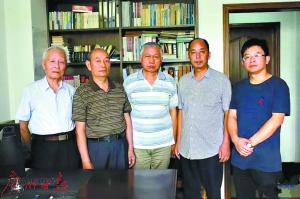
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骨干成员。
5位亲人死于鼠疫 对日索赔奔走20年
细菌战幸存者徐万智: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后,这段历史没人知道
今年77岁的徐万智是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他算是协会中年纪较小的,很多成员都已80岁以上。76年前,日军在常德投下鼠疫菌,他一家5位亲人丧生。从1997年开始,这位古稀老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诉讼,走村入户,起早贪黑,搜集日军细菌战的罪证。让徐万智担忧的是,20年间,参与对日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已有2/3去世。“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文、图 /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熟悉徐万智的人都说,“老徐在协会中是最卖力的,70岁了,在田埂上比小伙子跑得还快。”徐万智原籍常德汉寿县聂家桥乡雷家坡村,距离常德市区十多公里。
一年内5位亲人死于鼠疫
当时,他父亲兄弟二人,家里一共有12口人,徐万智是三姐妹中最小的。父亲徐明哲经常贩米到常德城里卖。但万万没想到带回来的却是一场灾难。
1943年春天,父亲挑米到城里卖,回家后就忽冷忽热,高烧不止,后来逐渐神志不清,还不停抽搐。家里人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到处求医。土郎中开了两副中药,但没见好转。过了两天开始屙血,脖子也肿了,浑身起疙瘩,前后过了四五天,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死后,二伯家的哥哥徐万勇和奶奶不久也发病去世了。
一家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感染了细菌。1944年,徐万智11岁的哥哥徐万成接着发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的时候嘴里冒着血泡,脸乌血。“这时,全家都病倒在床,动弹不得。邻居和亲戚找了几块破木板钉了个木匣子,把我哥哥抬出去埋了。”到家中参与抬尸的人,后来全都染病死了。
“道士都不敢来,怕染上瘟疫。”虽然过去了70多年,徐万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时农村迷信,也没有药,说这个人的魂掉了,去喊魂。晚上,家家都去喊魂,山野间,到处都听到村妇一边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撒纸钱。”
父亲死的时候还有棺材。等到二伯死的时候,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都是赊账。债主到他家讨账,把瓦片揭走,唯一的一头耕牛也牵走了。徐万智的祖父日夜哭,哭得眼睛都哭瞎了,母亲也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头发都掉完了。婶婶和他的两个女儿也病得奄奄一息。舅舅看到徐万智年幼,就接去他家。但到了舅舅家,徐万智也出现了一些鼠疫症状,后来舅舅给他吃一些草药,才算捡回一条命。但多年后,他仍需要经常吃药,身体异常虚弱,再也恢复不到正常人的体力。

徐万智
“死晚了就没人埋你了”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内大雾弥漫,早起的人们正在忙着各自的生计。忽然,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传来,城内居民纷纷像往常一样躲避空袭。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点才解除。人们发现,日军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它只在上空盘旋了3圈,撒下了一些破布,烂棉花、谷子、麦粒、黄豆等36公斤重带鼠疫的跳蚤,然后,飞机往石公桥方向飞走了。
当时的石公桥是湘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各地客商把米谷、棉花、布匹、鲜鱼运到湘西,把药材、土产运出去。就在日军投下这些谷子和布条后不久,经营食品、布料的地方就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别是卖肉、鱼、粮食的商铺里。“白天老鼠看到人却跑不动,毛发竖立如箭,眼睛发红,看起来十分恐怖。”
小镇的繁华加快了鼠疫的爆发。鱼档的老板张春国一家6口,不到半个月全死了,另一位开鱼档的丁常发,一家12人不到两天就死了11个,他儿子到外面读书才得以幸免。
当时天天都在死人,先死的用棺材抬去埋,棺材用完了,就改用门板,最后连抬尸的人都找不到了,就只好先挖一排坑,死了就用竹篮挑去埋,有的坑里埋四五个人,最多的一坑埋了8个人。“有不少患者的亲人对患者说,‘你快点死吧,死晚了恐怕没有人埋你了。’还有人感染了鼠疫,怕拖累家人,自己服毒自尽。”徐万智说。
常德县长岭岗是当时从湖北前往湖南运兵的必经之地。在此地的王家祠堂,染病的壮丁一批一批地死去,附近有一片荒地,后被用来埋葬尸体。壮丁死得太多,荒地埋满了,就往河里扔。“前后死了3000多名壮丁。后来,这一片晚上都没人敢经过,说是冤魂太多。”
当时负责火化鼠疫尸体的是保安司令特务排的班长文国斌。火葬炉在常德大西门外的千佛寺,用旧砖在废墟上砌了三座,炉高约3.5米,宽1.5米,深2.5米。上层是烧尸室的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点开始烧尸,第二天早上6点结束。每具尸体烧两个钟头,用松木劈柴200斤。每具尸体都用旧棉絮或被单裹得严严实实,分不清男女,只有从长短才看得出是成人还是小孩。班长一声令下,两人将尸体装入炉中,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火后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黑色的浓烟,一阵风就将浓烟吹了下来。“一阵阵烧焦的气味令人作呕。”尸体太多,烧尸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通宵轮班,但烧尸炉不停。其中一座烧尸炉用了才两个月,就烧塌了。“20世纪80年代,常德的部分村落依然发现有鼠疫菌。”徐万智说。
 湖南卫视经营体验类观察真人秀《亲爱的·客栈》,可谓是时下最火的慢综艺。前不久,同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师姐妹“北电姐妹花”,杨紫阚清子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以及呆萌搞笑的举止圈到了不少粉,网友纷纷刷屏:“为北电姐妹花疯狂打call!”
湖南卫视经营体验类观察真人秀《亲爱的·客栈》,可谓是时下最火的慢综艺。前不久,同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师姐妹“北电姐妹花”,杨紫阚清子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以及呆萌搞笑的举止圈到了不少粉,网友纷纷刷屏:“为北电姐妹花疯狂打call!” 由王珞丹、张嘉译主演的《急诊科医生》自上映以来就凭借专业的医疗知识,紧凑的剧情取得了一路飘红的收视率和持续不断的好评。而近日,片中饰演江晓琪的王珞丹和饰演何健一的张嘉译“历经26集”,终于为观众上演了一场“世纪壁咚”,引得一阵“发糖打CALL”。
由王珞丹、张嘉译主演的《急诊科医生》自上映以来就凭借专业的医疗知识,紧凑的剧情取得了一路飘红的收视率和持续不断的好评。而近日,片中饰演江晓琪的王珞丹和饰演何健一的张嘉译“历经26集”,终于为观众上演了一场“世纪壁咚”,引得一阵“发糖打CALL”。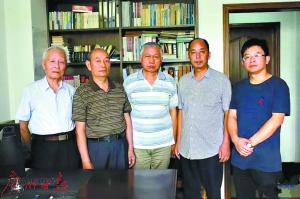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