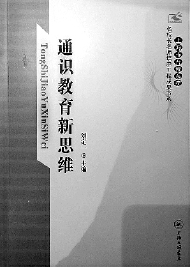

距今30多年前,我就读于华东师大一附中。我的母校是颇有历史的名校,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全市仅有十余所市级重点中学。当时上海有20个区县,平均一个区县还摊不上一所,而师大一附中就已然名列其中了。
长久以来,大众判断一所中学的“段位”高低,最重要的标准是升学率。我认为,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当年考生远多于今天、高校远少于今天、招生规模远小于今天,升学之难真堪比蜀道之难于上青天。师大一附中的升学率则傲视群雄。就拿我参加高考的1984年来说,全年级4个班,每班40人,共160人,除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留校担任团干部未参考,一位平时成绩不错的同学马失前蹄未考上(今天也出色地工作在金融岗位上)以外,其余158位同学全部考上大学,被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中科大录取者,总以几十人计。外语类的上海前十名,我所在的班级里就有3名。
升学率之高,当然离不开有效的应试教育。我至今坚持认为,不可简单化地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对立起来,并贬低应试教育。这样做不符合实际,违反常识,有悖情理。在我看来,应试乃是最基本的素质之一。这里不是展开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只想说,当年师大一附中的“素质教育”也非常成功。我们的体育活动、课外兴趣活动,恐怕远比今天的中学丰富得多。我本人就是学校田径队的中长跑队员(其时的师大一附中也以田径闻名),专练800米、1500米,有不短的一段时间,我的体育老师黄顺奎先生,每天一大早骑车陪我,先完成一次从中州路到复旦大学的折返跑。全程恐怕接近一万米吧,这就为我打下了受益无穷的耐力基础。此外,我还参加了历史、生物等好几个课外兴趣小组。这些都是中学时代留给我的美好回忆,我至今感恩、感念不已。
30多年的师大一附中何以臻此?当然,因素有很多,然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拥有一批特立独拔的极其优秀的教师。他们有情怀、有水平,都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教育家。本身承担教学任务的科目不必说了,这些老师还都各有专长,且水准绝不低于高校的专家教授。
谨恭举数例。
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独创一套历史教学法,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专著,更将历史教得引人入胜。我最早听到恩师季羡林先生的名字和著述,初步了解梵文、巴利文研究,就是拜郝老师之赐。后来,也是在郝老师的指导下,我选择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作为自己高考的第一志愿。
语文老师陆继椿先生,自己编撰了一套语文教材,不仅师大一附中用,好多别的学校也用。语文老师吴侃先生,专研历代笔记小说。俄文老师张思中先生,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外语教学法。这三位老师并没有直接给我所在的班级教过课,但是,课余都“有教无类”,不管哪个班级的学生,都可以去找他们聊聊,各位老师自然是不吝赐教。我获益良多。
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学生的造就,真正是当得起“功德无量”四个字的。
数学老师刘定一先生就是这个教师群体的一员,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还在我就读于师大一附中的30多年前,刘老师就已经是学生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刘老师还兼着另外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并不教我们数学,只是偶尔给我们班级代过不多的几次课,因此,我与刘老师的接触不多。而且,当年的刘老师以严厉著称,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挟着教案,不苟言笑,步履舒缓,俨然踱过,一般都是赶紧闪到一边,恭敬让道。
不过,传奇又使得我们对刘老师绝不陌生。我们这批一附中学子大概都知道(可能不完全是事实,我们好像也没有人敢去问刘老师),由于所谓的“出身问题”,刘老师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凭着超越常人的天资与毅力,硬是靠了自学,成为一名文理两通、外语兼擅的名师。不仅如此,刘老师还挺身学术前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一代系统论学者之一。30多年前可不是今天,那正是出版最困难的时代,将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是多少学者终身未必可及的梦想,而我们的刘老师,早就出版了有关控制论的论文、专著、译著。套用今天学生的一句话,在我们心目中,刘老师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就我所知,我的许多同学就是以刘老师为楷模,立志成为科学家、学者。其中不乏考入当年全国瞩目的中科大少年班者,成为世界著名科学院院士者。拥有这样的老师,是一所学校、几代学生的福分。
1984年后,我北上求学,不久留学欧洲,后又辗转国内外,与一附中的老师们久疏音候,请教无由。等返回上海忝列复旦大学教席,已是年过四十。我和一附中的老师们很快就恢复了联系。古语“四十不惑”,而我疑惑日多。少年时代的老师们,如郝陵生先生、刘定一先生,又成了我请教的对象。师恩浩荡,泽被远矣。
刘老师早已是特级教师,是上海乃至全国的一代名师。但退而不休,依然主持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我偶然知道,近年来,刘老师致力于《论语》研究,别开蹊径,从系统论、逻辑结构等角度,对《论语》的文本、语句、言辞,进行突破性的重构与阐释。听说刘老师开设《论语》讲座,作为学生,我恭敬前往聆听,真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许多阙疑扞格之处,在刘老师的阐释中,文从字顺,语气完足,篇章自成。在刘老师的课堂上,我如入宝山,目不暇给,欢喜赞叹,钦敬叹服。
《论语》诞生于轴心时代,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大经大典,其重要性自然不待辞费。刘定一先生的阐释,一定会与时下通行的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刘殿爵先生英译《论语》、李泽厚先生《论语今读》、孙钦善先生《论语本解》等并肩,而成立一个全新的系统,在源远流长的《论语》学术史上,彰显典范式的开创意义。我期待,并且相信,越来越多的读者会认同我的看法;我期待,并且相信,在地不爱宝的今天,不久的将来,就能有出土文献证实刘老师的阐释和研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论语简明读本》并不是刘定一老师论语研究的全部成果,而只是其简纲。作为一名老学生,我有幸拜读过刘老师的部分书稿,精义络绎,不可名状。我盼望,刘老师的《论语研究》也能够很快问世,以飨读者。
光阴荏苒,作为学生的我,也已经年过半百。我一附中时代的老师们,都已经年过古稀,或登耄耋了。他们是中国教育的当之无愧的梁脊。各位老师更是我毕生的楷模榜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者系著名学者 复旦大学教授)
 今年2月,UFC(终极格斗冠军赛)签下了中国MMA羽量级代表人物王冠,并为他安排了被誉为“皇家李小龙”的美国人卡萨雷斯作为对手。在世界上最顶级、规模最大的职业MMA赛事中,首秀就遭遇曾排名前15的选手,王冠心里晃过一丝惊讶,马上转念:“上来就打强手的机会不是谁都有,打赢了在行业里影响力将非常大。”
今年2月,UFC(终极格斗冠军赛)签下了中国MMA羽量级代表人物王冠,并为他安排了被誉为“皇家李小龙”的美国人卡萨雷斯作为对手。在世界上最顶级、规模最大的职业MMA赛事中,首秀就遭遇曾排名前15的选手,王冠心里晃过一丝惊讶,马上转念:“上来就打强手的机会不是谁都有,打赢了在行业里影响力将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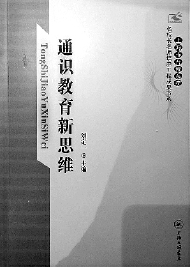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