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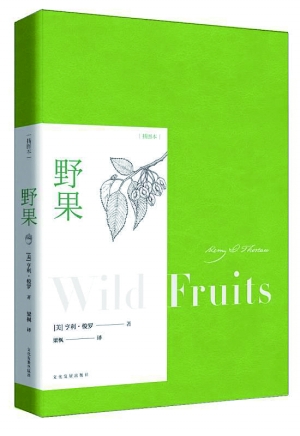
提起亨利·梭罗,中国读者马上会想到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但事实上,梭罗在那里只坚持了两年,而他把生命最后的10余年,交给了故乡康科德镇的乡村田野,于是便有了《野果》(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
在《野果》中,梭罗记录着新英格兰大地上众多野生的植物,讲述它们与人类互动的故事。
《时代》周刊曾评论称:这是我们这位伟大的自然作家最后的成果,《野果》堪称美国福音──为我们展开自然的神圣画卷,从每一页上,呼之欲出的张力,那是身为自然主义者的梭罗和身为自然传教士的梭罗之间的张力。
该如何接受这份“最后的成果”呢?该书的中文译者梁枫做出了精彩的解读。
那些野果就长在我的房前屋后
梭罗在我的心目中,首先是一位有点古怪的邻居。
他的故乡康科德镇,与我马萨诸塞州的家相距不远。对于新英格兰这片土地,梭罗始终怀有一种近乎执拗的爱,坚信此地“方圆几十英里,即有世上最美的风景”。
他笔下的瓦尔登湖、鳕鱼角、怀特山脉、缅因森林等,格调清冷却又色彩斑斓,是我周末和假期常去徜徉的地方。《野果》书中所描述的各种植物,许多也生长于我的房前屋后,读来自是十分亲切。
译《野果》的过程,也历经春去秋来,方圆数里内果真像书中一样,从早春的蓝莓到深秋的松果,其间穿插着沁凉的西瓜、纷飞的马利筋、丰硕的马铃薯、金灿灿的南瓜等,活色生香,不一而足,与百年之前似乎并无二致。碰到书中某种野果的形态不太确定时,只消起身到后院寻觅一番,多半能找得到些线索和痕迹。
他的记录准确又饱含诗意
在我心目中,梭罗也是一位高冷范儿的学长。
作为他的哈佛学妹,我的脚步比他晚了一百多年。《野果》一书中严谨的学术精神,追根究底不盲从的治学态度,体现出的是一脉相承的精神气度。
在梭罗生活的年代,美国植物学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相关著作十分有限,学科研究体系也并不完整,他大量精准的第一手观察、认真保存分类的植物标本以及详尽的记录与描绘,为研究19世纪中期新英格兰植被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与此交相映衬的,又有丰富的史料与旁征博引,梭罗将不同来源的素材相互佐证,以得出尽量准确并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书中将数年经验合并一处,并按野果种类分列成志,观察细致入微,记录准确翔实,笔端又饱蘸诗意。开卷细读,只见自然之画面如一卷轴,在眼前徐徐展开,质地绵密,格调清新,纤毫毕现,万物结实均自有其时节与次序,繁衍传承各得路数并自有妙招儿。
这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梭罗
对于喜爱梭罗的读者来说,本书中展示出的,是一个颇不同以往的梭罗。他的影像不再只是瓦尔登湖畔小木屋里的隐士,也不只是因抗拒人头税入狱而后写出《论公民的不服从》的斗士。这本书里更多的是一个日常的梭罗,“上午和晚上伏案写作,用漫长的下午在野外散步”的梭罗,作为博物学家和超验主义者的梭罗。
《野果》是梭罗宏大的计划的一部分,离世前只完成了冰山一角。本书的写作大约开始于1850年,此时,他已自费出版了第一本书《河上一周》,并宣布了《瓦尔登湖》即将出版,正在寻找下一个题材。在一段时间的求索之后,梭罗在1851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深信,人所从事的雇佣工作是不适宜的——人不该用那种方式度过一日。倘若凭着耐心的观察,我能找到一线新的光明,发觉自己瞬间飞身跃上了毗斯迦山,令这原本死气沉沉的世界重又变得神圣并焕发生机,那我将何乐而不为——何不从此成为一名守望者呢……
观察,并描述,一切我在自然中发现的神性。我的职业将永远是在自然中专注地寻找上帝——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此后,梭罗找到了下一步写作的使命,即细致观察并忠实呈现自然中未经他人过滤的、无中介物的神性。《野果》一书,正是将这一使命付诸实践的代表作品。
文/梁枫
(本报有删节,标题、小标题为本报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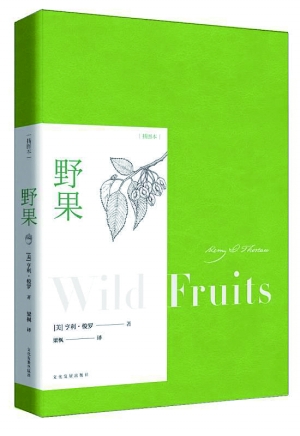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