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更多 |
法学家任职最高人民法院又迈出重要一步。近期,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一批人事任免名单,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的林维、刘广三、刘敬东、王锡锌、冯果等5位法学专家,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相关业务庭副庭长。这是自上届人大2012年底任命3位法学家任职最高法院副庭长以来,第二轮法学家担任最高法院副庭长职务。(财新网4月26日)
法学家入职最高法院,最直接的好处,诚如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所言,“有利于更好地在法院司法制度建设、司法解释制定、司法政策研究、重大案件审理和司法课题调研等方面,充分听取和吸收意见建议,更多地将最新法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司法实践、服务于司法实践,帮助审判人员开拓视野、提高能力。”而且,推动法学家与法官角色的转变,走双向交流之路,也“有利于提高法学教育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法学家进入最高法院之后,作用究竟发挥得如何,因为资料不足而难以实地考证,但从这批法学家的任职信息看,用人单位应有不错的评价。比如,在2012年年底时,仅3位法学家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到今年则又新增5位,使得最高法院副庭长中出身法学家的占到了近20%。平心而论,这的确是个颇为可观的比例,倘若实际成效不佳,想必有关部门也不会如此大幅度“扩招”了。
不过,身为法官却不能主审案件,也是法学家任职最高法院一大“憾事”。根据2011年中央政法委、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2012年7月最高法院制定的《关于建立人民法院与法学院校双向交流机制的指导意见》,被集中邀请的挂职法学家,他们虽然可出席有关会议、参加司法政策研讨、司法解释制定、重大案件研究、司法改革论证等工作,但实际上“不会让他们主审一个案子”。
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法学家在理论研究上的特长,另一个没有提及的考虑因素,则是“隔行如隔山”。因为法学家在院校从事教学工作,这与司法审判有着明显区别。正因为“被中意”于提供理论支撑,被视为双向交流的对象,这些进入最高法院的法学家不必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也给他们的身份合法性引来非议。毕竟,《法官法》中明确规定了初任法官“硬件”。
如果说,我国法学家任职法官还带有某种“临时”色彩,一些国家的法学家与法官互换渠道早已畅达。亨利·布雷克顿、爱德华·柯克、威廉·布莱克斯通、威廉·默里、布鲁汉姆等法官兼法学家,都以其不朽的学术成就和经典判例载入法律史,而现实中也不乏法学大家成为法官的事例。
法学家与好法官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在最高法院这个层级,只有介入司法实务尤其是案件审理,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学家的理论功底,产生准立法的辐射效应。在去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今年2月26日,最高法院又发布深改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遴选为法官的制度”。由此,也期盼随着改革立法的深入,让真正“永久牌”法学家型司法者走上前台。
| 中国青年报:认真对待国庆特赦的建议 2009-02-19 |
| 新华网:修改《拆迁条例》重效果为根本 2009-12-17 |
| 中国青年报:认真对待国庆特赦的建议 2009-02-19 |
| 新华网:修改《拆迁条例》重效果为根本 2009-12-17 |
| 广州日报:有一种不好意思叫徇私枉法 2010-05-05 |
| 杨 涛:制约住权力比废除贪官死刑更重要 2010-08-31 |
| 声音 2012-07-05 |
| 练洪洋:从“少杀、慎杀”中感受人权温度 2013-05-15 |
| 王 琳:放开公益诉讼才符合“环保国策入法” 2013-06-27 |
| 千龙网:修改条例能否敲响暴力拆迁的丧钟 2009-12-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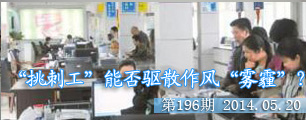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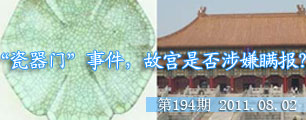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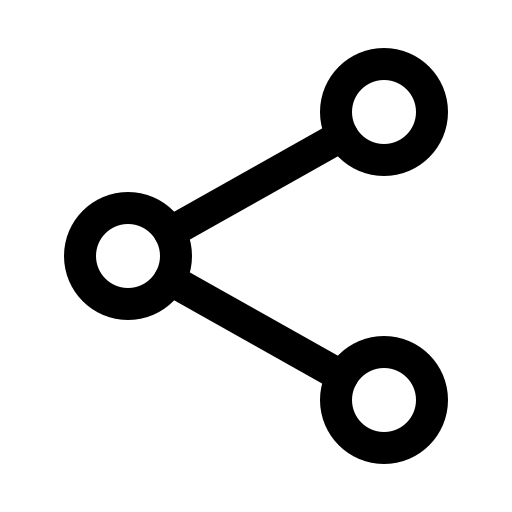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