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之乐
著书、写文章是为了更好地教书,这是胡先生做学问的初心;构建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则是他作为教育学人的使命。
大学生活为胡先生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他的人生也自此迎来了新的曙光,揭开了新的篇章,开始了有定向意义的新生活。这不仅确定了他以后的从教之路,也决定了他将要以教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作为一生的学术事业。
胡先生和教育学的相遇就从这里开始。
大学四年的学习与生活,不仅让胡先生获得了专业的成长,也让他发现了教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当时教育系所讲授的各门教育学科中,包括苏联专家讲授的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在理论上都存在很大的偏颇和不足。但要研究精到,成绩显著,不仅需要激情和努力,更需要聪慧的头脑、宏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以及能坐十年冷板凳的坚守。
为此,胡先生暗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建一个较为完备的教育理论体系。
下决心不难,但要做到却绝非易事。无数次披星戴月,无数次挑灯夜读,胡先生总会沉静自问:“我凭借什么可以做到呢?我的条件和功夫又在什么地方呢?”寂静的夜晚,他的思绪在头脑里剧烈地翻腾、碰撞,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推门出来,清冽的空气让胡先生异常清醒,大西北特有的璀璨星河让他豁然开朗:“我别无依靠和凭借,我唯一依靠和凭借的是我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好学和深思。我的功夫并不是在教育学自身,而主要是在‘诗外’,即陆游说的‘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诗外’。”
多年持续不断的与书为伴,有两门学问对胡先生思维体系的形成影响深远,一是文化学,二是宇宙学,其中尤以宇宙学为最。他曾说:“我的教育理论能被整合成一个体系,靠的就是文化学、人类学所基于的这种宏观学术力量。”
宇宙学更是为胡先生展开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宏画卷:“我了解了这些知识理论,看到宇宙大爆炸后所呈现出的图景,真是为之欣喜不已,拍手称快,感慨万千,犹如拨开了云雾见到了青天,打开了眼界,精神为之一振,真正感到心明眼亮了起来。”这种宏大视界,让他拥有了一种站在宇宙的云端俯瞰大千世界的哲学理念,而这种理念投射到教育学上,便对这一领域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胡先生的教育学研究,均属于宏观教育学、理论教育学研究,其深层次原因便在于此。
20世纪80年代初,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能为这个新的时代做些什么?能为这个时代的教育学做些什么?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教育学应该承担怎样的时代使命,完成时代赋予的哪些职责?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胡先生对自己所追求之事越来越坚定而清晰:“我必须把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给教育学一个宏观、完整、全面、具有系统性和学理性的概括和说明,从而给教育学一个恰当的定位,并透显出教育学的理论价值。”
从此,胡先生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座右铭,开始了对教育学体系的反思与建构,先后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1981)《教育起源问题刍议》(1985)《论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1985)《论教育的自在与自为》(1988)等文章,从理论源头探索教育的本质与属性、存在与发展。
1990年3月,胡先生发表《教育学概念和教育学体系问题》一文,引起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强烈反响。他在对教育科学进行总体研究的同时,还对若干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先后发表《论教育现象》(1991)《论教育、人与社会的关系》(1992)等50余篇论文。尤其是他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理论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常常被学界同行作为经典引用。他关于教育现象的系统研究,在教育理论界也影响深远。
1998年,在40多年沉淀与思考的基础之上,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胡先生出版了教育学巨著——《教育学原理》。这是他教育思想的结晶,标志其教育学思想体系的成熟。在这本书中,胡先生从教育学的概念、对象到内容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对传统教育学基本概念的误区中引申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勾画了整个教育学原理结构延伸的脉络,尤其是对传统的拘泥于一隅的教育学理念大胆突破,让人耳目一新。
胡先生认为:“教育学研究的出路要面对现实,深入历史,归于实践。为了达此目的,我们的教育学研究应当首先清除在知识构成、研究兴趣上的片面性和隔阂,应当使教育学著作在基本理念和原理、编排体系、论证方法、表达方式、文字风格、思维水平上,都有适应当今教育改革实践要求的突破和进步。”他对中国教育学出路的独到见解,不仅为其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完成《教育学原理》书稿后,胡先生感叹:“想到多年来我为此付出的诸多孤寂、劳作与艰辛,特别念及昔日那几十年令国家、民族都深受屈辱和我个人所曾亲历的苦难的岁月,真是感何如之!奋何如之!幸何如之!”由此可见,走学术道路的他,并没有放弃家国情怀,依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社会责任紧密相连。
《教育学原理》出版后,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东方杯”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一届甘肃省优秀图书特别优秀奖、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理解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决不随波逐流,更不囿于陈说,是胡先生一贯的学术品格。他说:“理论研究要说理,要讲道理,教育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体对教育现象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盲从,从于权威,从于利益,从于时尚潮流,从于众口一词,或从于个人的滥情。”这是他《教育学原理》《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人生与教师修养》《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问世的根本动力和目的所在。
文如其人。一般来讲,治学与为人是统一的。胡先生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实际上是他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现。他为人真诚谦和,待人感情真挚,做事踏实严谨。在他看来:“人本身永远是学生,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与他人都是老师,人的短暂一生,该学习、该探索的东西实在太多,永无止境。”
言行相顾。胡先生的言行均发自本心,无论环境怎样变化,他都力求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他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尊重人情人性,一贯坚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言之有文。他曾说:“我非常欣赏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法则,面对苍茫的宇宙和浩渺的时空,我乐意接受这种精神法则的支配。因为正是这个,才意味着学术真正的尊严、公平与价值。”
胡先生所有的论述,皆发为心声,不遮掩,不妄言,真诚之品格溢于字里行间。
如果我们对胡先生的学术轨迹进行一个梳理,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他1996年出版《人生与教师修养》,时年69岁;1998年出版《教育学原理》,时年71岁;2001年出版《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时年74岁;2005年出版《教育理论的沉思与言说》,时年78岁。
同时,胡先生不断在权威期刊上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2012年,85岁的他在《教育研究》第12期发表《王国维与中国教育学术》一文。2013年,86岁的他将自己的《教育学原理》进行修订,增加3万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在《中国教育科学》(第二辑)发表了近三万字长文《关于什么是教育学的问题》,2014年则出版了《陇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
2018年,胡先生91岁。这一年是先生学术活动比较活跃和学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年。从学术活动和成果来讲,3月,他应邀到山西师范大学为师生作《关于教育学和教育的问题》的学术报告;11月,他在《中国教育科学》(第2辑)发表了2万多字的文章《读书、教书、著书: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从学术影响来讲,9月,《西师学人》的视频风靡全国,分别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等媒体播放;2018年11月1日,《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报道了胡先生的教育事迹。2019年6月,92岁的胡先生在《中国教育科学》(第一辑)发表《关于什么是儒家传统修养的学理解读》;他的著作《文化与生活——我的生活印记》将于2019年年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如今,胡先生仍不遗余力地研究教育文化。他说:“研究教育学是有方法的。既要站得高,又要扎得深,既能大至宇宙,也能深入到人,研究人性、研究人心,用人、人性、人心和人心产生出来的文化来解释社会和历史。”
耄耋之年,自当静养,而胡先生却老当益壮、勤思善著、乐此不疲,一如既往地追求他的学术生活,演绎一个学者的生命意义。
1994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顾明远先生曾这样评价胡先生:“好学深思、刻苦钻研,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40年的磨练,始终坚持不懈,严谨治学,无论在教育学原理,还是在人生哲学等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和深邃的创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0多年来,时有见地卓越的论著问世,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影响深广,声名卓著。”时过25年,认真阅读和体会胡先生关于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独特见解和卓越贡献,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评价的中肯。
胡先生一向注重为学与为人的关系,“顶天立地做人,继往开来创业”,把做人看成做学问的根本,他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做人做不好,投机取巧,做自以为聪明的小动作,那么做学问也做不好,做人要实实在在,做学问也要实实在在。”
可以说,胡先生与书相伴的心路历程、治学精神与人生境界,犹如西北教育的“胡杨魂”,对每个后世学者来说,都是永恒的感召。
作者:高闰青,女,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教育学博士,2005年师从胡德海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特岗计划”实施成效研究》《“以人为本”理念及其教育实践问题研究》《胡德海教育学术思想研究》《家庭教育:为孩子的成长打好底色》等著作。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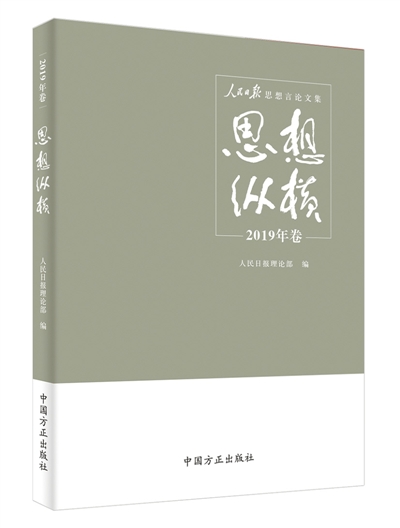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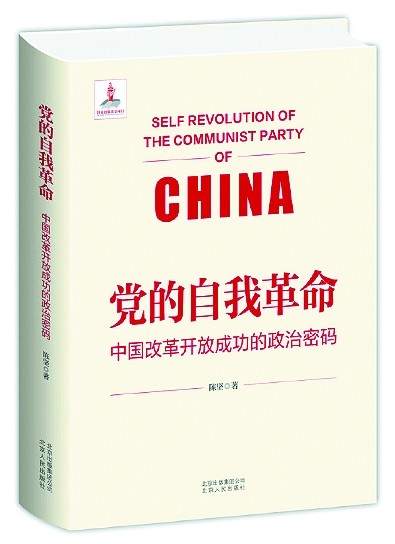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