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 难
春天的阳光从邻近山头
开始把积雪往山下驱赶,
雪水汇聚成混浊的溪流
注入那已被淹没的草原。
大自然面带明丽的笑容
迎接一年之晨,睡眼惺忪,
天空泛出蔚蓝,闪烁光芒。
树林中依然是稀疏透亮,
已现出毛茸茸一片绿意。
蜡质的蜂房里飞出蜜蜂,
飞去征收那田野的贡奉。
山谷雪水退尽,斑驳绚丽;
牲畜在田野上阵阵叫嚷,
夜莺在夜静时纵情歌唱。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1节
说干就干。王智量首先从书中选出十节,用它们当作试译,来确定翻译这整部书的方法和原则。几个月后,他已经翻到第二章的中间,一共译出六十多个十四行诗节。
1956年,何其芳先生写了一篇长达八万余字的名文《论〈红楼梦〉》。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对《红楼梦》作了精细的思想和艺术分析,还对其中一些主要的人物给予了准确评价,对当时与以往红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市民说”、后四十回的真伪问题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篇长文,充分展示了何先生的才情、学力、学风和品格。
何先生把王智量翻译的那十节《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节作为引文,放入《论〈红楼梦〉》里。那是第八章的第46节——
对我,奥涅金,这豪华富丽,
这令人厌恶的生活的光辉,
我在社交旋风中的名气,
我时髦的家和这些晚会,
有什么意思?我情愿马上
抛弃假面舞会的破衣裳,
抛弃这些烟瘴、豪华、纷乱,
换一架书,换个荒芜花园,
换我们当年简陋的住处,
奥涅金啊,换回那个地点,
那儿,我第一次和您见面,
再换回那座卑鄙的坟墓,
那儿,十字架和一片阴凉,
正覆盖着我可怜的奶娘……
普希金在这节诗中出色表达了达吉雅娜的浓郁情感,何先生以此来阐释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描绘,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来之笔。先生在文章中说,这节诗是“诗中之诗”,是最美的诗。
王智量深深领悟到,何先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方式,是对他辛苦付出的莫大鼓励和亲切关怀。从这天起,他更加满怀信心,“大胆地、老实地、下功夫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但是,没过多久,便大难临头了。
1958年春天,王智量被打成“右派”,随后的20年间,他先下放到河北山区改造,后被发配至甘肃农村,妻离子散。王智量饿病交加,数度陷入生命的绝境。
王智量记得,1958年5月,就要被送往河北东部太行山区的前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北京中关村中国社科院社会楼第三层,安静极了。孤独的他正在发呆,忽然何其芳先生走到他的身后。
当王智量转过身去,发现何先生正立在他的背后,他俩面对面,吓得王智量都不敢说话。而让王智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先生用浓厚的四川口音,低声而又严肃地对他说:“《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话音字句,音容宛在,王智量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王智量流出热泪,伏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之后,他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了本来不敢带的那本已经被他翻烂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单行本和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行李中。
第二天,王智量被带到河北省建屏县(现为平山县)劳动改造,分配在西柏坡村附近的小米峪村,落户在老党员王良大伯家中,和其子海兵同睡在驴圈旁的一张土炕上。
那段时期,王智量每天不管干什么农活,总是一边干、一边心里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无论是蓝天白云,还是阴云密布,他总是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旱稻稻种的田垄,一边借助这一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四音押韵规律,然后再一句句地把原诗,按照他预先定下的方法和原则,在心中翻译成中文。
伴着脚下的节奏,一句句诗文就这样均匀起伏地流淌出来。
待到晚上,等海兵弟弟睡着了,王智量不是在煤油灯下,继续细读一节节《叶甫盖尼·奥涅金》,心中琢磨着如何翻译,就是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包装纸、卫生纸和一片片香烟盒上。
就这样,珍惜分秒,几乎一天都没有白过。
铜 像
啊,我的读者,是敌或是友,
无论你属于哪一类,现在,
我都想和你友好地分手。
再见了。无论你上我这来,
是想从这潦草的诗节里,
寻找那激荡不安的回忆、
活跃的画面、工余的休闲,
寻找些聪明机智的言谈,
或是寻找些语法的毛病,
但愿你能在我这本书中,
为了消遣,或是为了幻梦,
为了心灵,为杂志上的争论,
找到点什么,哪怕一小点,
让我们就此分别吧。再见!
——《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49节
1960年年底,王智量从兰州出发,睡在硬座车座位底下来到上海。他的全部行李是几袋书和一个装满各种各样碎纸片和几个小本本的手提包,那是一节节《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稿。
王智量的哥嫂收留了他,给了他一条生路,也给了他继续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条件。
1962年年底,王智量与恩师余振先生,在上海重逢了。之后,他每周都要到余先生家去一两次,在先生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参考书,不停对《叶甫盖尼·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
余先生的家在汾阳路口,推开窗子,可以看到坐落在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的街心三角地带的一尊精致的普希金铜像。这是一尊胸像,胸前飘动的领带、精致的面容以及那双炯炯有神、凝视远方的双眸,生动刻画了普希金不屈的伟大形象。
这尊铜像,建立于1937年2月10日,是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造的,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44年11月被拆除。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又于1947年2月28日,在原址上重建,由苏联雕塑家马尼泽尔创作。1966年,铜像在“文革”中再一次被毁。1987年8月,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之际,铜像第三次在原址落成,至今完好无损地矗立在街口。
在世界各地,普希金雕像数不胜数,但像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建了拆、拆了建,可能也只有这一座吧,从中可以看出普希金这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同样,在王智量与余振心中,普希金是神圣的偶像。尤其在他们的苦难时期,仰望普希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师生二人精神最沉醉的时刻,不仅纯净心灵,还明晰理想信念的方向,更是支撑他们生活力量的源泉。
在上海无业的艰难日子里,王智量在几所中学做过代课教师,同时以每千字两块钱的价格给上海科技情报所翻译外文资料,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
余振见王智量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自己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第二编,送到福州路卖掉,几百块钱送给王智量,让他安心养病和好好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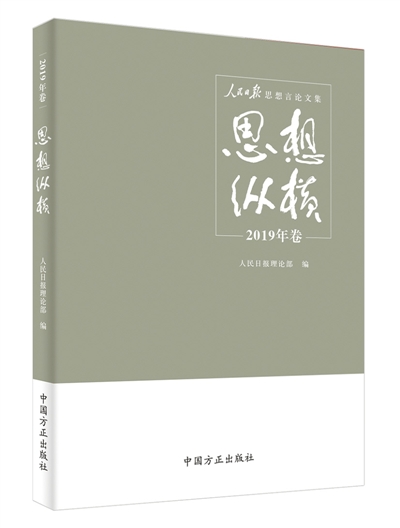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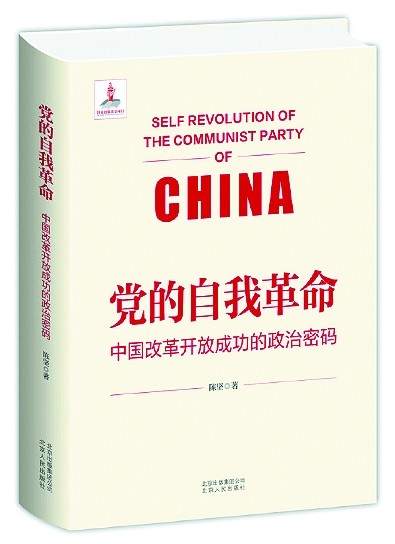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