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尤其在中共党史方面著述丰硕,有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学界空白,在方法和风格上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研读金冲及的中共党史作品,感觉其在中共党史治学中有如下突出特点。
聚焦重要问题
金冲及认为,研究的第一步是选择题目,选择题目首先要考虑问题本身的重要性,首选重要且为人所关注的问题。对于“邻猫生子”之类的研究,他告诫说:这易导致“在总体上流于碎和散”,“如果整体上或者占主流地位的趋势长期停留在这种状况,以为史学之能事尽于此矣,也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史学的发展受到局限。”金冲及的专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即是选择题目的典范。
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一书的开头,金冲及就抛出了一个为多数人所关注的问题:194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而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这种奇迹是如何在一年之内发生的?在40万字的著作中,他从政治到军事,从内政到外交,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到国统区的爱国运动,娓娓道来,把历史的复杂性和前进中的曲折展现得淋漓尽致。开篇提出的重大问题水到渠成地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金冲及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并没有因为问题相对宏观而流于空泛,每一章节都充实而饱满,读来引人入胜。
谨守“论从史出”原则
金冲及认为:“一种是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穿靴戴帽’式地硬贴在对历史的叙述上,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另一种是把一些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理论框架硬套到中国历史叙述头上来作为装饰。”“这类廉价的、费力小的办法未必能真正帮助我们加深对所研究的历史事件的理解。”在研究实践中,金冲及始终严守“论从史出”的原则。
要真正做到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不带先入为主的观点,着实不易。金冲及曾结合新疆历史的某些片段对笔者举例:有的研究讲到辛亥革命前后,将杨增新完全描述为军阀和反动人物。诚然,作为清政府任命的新疆官员和拥护袁世凯并因此受封的一等伯爵,杨增新甚至取消了在辛亥革命中成立的伊犁临时革命政府。这些都是事实。但仔细梳理史实不难发现,当清政府被推翻、社会大动荡时,新疆面对的最大危险,一个是沙俄的觊觎,一个是新疆境内民族矛盾的大规模激化。而杨增新虽然是一名军阀,却比较稳妥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所以,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应该既写他的反动方面,也写他的贡献方面。总的说来,应该更多地给他一点肯定。这个例子对于在研究中时刻警惕先入为主的想法,真正严格做到“论从史出”具有启示意义。
重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
金冲及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要重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这个观点,他说:“事情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很多事实的演变,在事后因为结果已放在那里,似乎很清楚明白。但历史上那些当事人却没有如此幸运。他们作出决断时,通常都面对着许多未知数和变数,有时还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后人研究这些历史,就得还原到他当时那种复杂而矛盾的处境中,设身处地地去努力理解它。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这些复杂而矛盾的诸因素,往往既对立又统一,同时存在,相互作用,以至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因此,在研究工作中,就要多花些力气,对事实细心地从多方面考察,反复斟酌。
金冲及同时告诫笔者: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确实存在过一些过分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的现象,即便如此,也不可把以前说得少的方面拔得过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历史的发展终究还是有着主流和支流的区别,忽视支流固然不可取,但为求“新”而非求“真”,甚至哗众取宠地一味强调支流,把本末倒置过来,则更不可取。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尽量全面、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与此同时,在表述时,则要尽量提纲挈领、去芜存菁,把复杂的问题尽量用简单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抓得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
上升到理论高度
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金冲及大部分著作可以归入史学研究范畴,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理论文章。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长于叙事,理论工作者擅于论理,两者无论在所需知识、使用方法还是关注重点上都有所不同。但金冲及却可跨越两个领域,并在理论界也独树一帜,写出很多传颂一时的雄文。比如,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工作方法的几个特点》,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金冲及在《求是》发表了《五四运动百年祭》。这些文章能从历史的细节中跳出来,从更大视角和更远距离来审视,逻辑清晰、语言生动、气势磅礴,而且“笔端常带感情”。论人,能切中要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样。论事,能把事情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说得明明白白。论理,能娓娓道来,就像一位长者在心平气和地讲述,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使道理显得血肉丰满而让人触手可及、易于接受。
文字讲究而平实
对于文字,金冲及一直极为重视。他说:“这里说的是文字要‘讲究’,不只是说要‘注意’。”金冲及认为,文字的讲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写文章要处处为读者着想”。这自然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文字能吸引人、说服人,要准确、鲜明、生动等等。但有一点在金冲及的文章中一以贯之,尤值得学习,就是语言平实、口语化,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平时不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更不用那种需要耐心辨析才能明白具体所指的“西式句子”。金冲及从不用生僻的字、词和佶屈聱牙的句子来故作高深,而是用平实、简练的语言将历史上一桩桩的事和一个个的人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仿佛置身历史现场。例如,在120万字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一开篇金冲及就颇带感情地说:“我们如此熟悉、仿佛依然生活在其中的二十世纪,转眼间已被称为‘上一个世纪’,完全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让人一下子就有了对逝去的一百年的留恋和怅然,油然而产生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接下来便直奔主题:“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在简要叙述了这一百年中国人走过的道路之后,金冲及就像抹去灰尘后小心翼翼地向读者掀开一本大书,说道:“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全文没有故作高深的概念堆砌,没有激昂澎湃的情感抒发,却引人入胜。由此也不难看出:真正好的文章,好在立意,好在结构,好在叙述准确、鲜明和生动,也好在逻辑清晰和说理透彻,而绝非是有几个新颖的概念、加一点似是而非的理论、堆几句华而不实的形容词就能做到的。
金冲及的治学用事实告诫我辈学者:学问,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来做,除此,没有任何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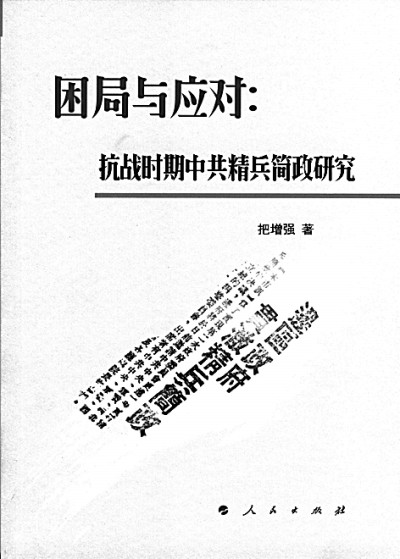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