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到: | 更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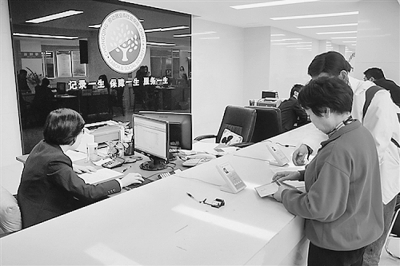
强调社区的自我管理、推动实质性社区的发展,是新一轮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图为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社区居民服务,该中心将社区的大部分行政职能加以集纳、整合,以求归还社区的自治功能。 图片来源:重庆日报
“改革”与“市场”,无疑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键字眼,而“治理”的出现,则成为整个报告的亮点之一。这几个词涉及到当下中国一个非常紧迫的命题:在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过程中,如何通过社会治理体制等各项具体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优胜劣汰是市场的本能。如果说市场会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风险,原因并非市场有错,而在于我们并没有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未来更加深化的市场改革中,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变得非常重要。这一建设指向三个基本任务:一是在政治层面,完善政治协商机制,通过程序来强化公共权力责任,以应对社会压力;二是在行政层面,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直接回应社会需求,消弭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过度悬殊的利益分化;三是在国家与社会交界处,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便利,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和社会管理体制不同,社会治理体制的提法强调的是多元化手段的使用,强调的是双向对等沟通。在一个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政府、市场、社会将构成良性合作关系。因此,与带有一定管控意味的社会管理体制比较,社会治理体制更关乎“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全新的社会治理概念背景下,新一轮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有几项重点工作需要特别指出:
重点一:启动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在以往的改革中,我们经常说经济政策,很少说社会政策,原因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做大蛋糕”,但今天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则是“分好蛋糕”。事实上,随着市场化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未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如此,一些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还有所加大。为此,我们必须导入“社会政策”视角,重启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并进行专业化的、精细的社会政策设计。显然,新的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是三中全会报告所折射的理念。
重点二:推动实质性社区发展。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场域,但在我国改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并不是扮演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角色,而是主要发挥着国家管理单元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社区的功能。这其中,要强调社区的自我管理。当然,社区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社区不属于公共管理的范围,比如商品房小区的公共安全也属于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而重要的是,在政府供给的同时,社区也可以通过自组织的形式补充供给。如何发挥社区的这种自我管理功能,需要社区居民具有充分的社区精神和志愿精神。
重点三:关注业主议题及其相关的社会冲突。在中国住房改革之后,国家不再直接参与房地产领域的分配活动,城市居民得以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住房需求选择住房,“业主”一词渐入人们视野。从制度层面来看,业主议题不能再混同于一般的公民个体,而应该成为单独议题,并以此为基础理顺我们现有的各种相关法律体系。必须在物权法的精神下,梳理现有各种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完善对业主物权的保障体系,在制度层面上疏导可能发生的各种业主物业冲突。在邻避冲突解决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的是,必须在法律和制度上将各种具有邻避效应的公共设施列入决策过程中,不能再以模糊的“尊重多数人利益”而牺牲邻避设施所涉及的少数人利益。
重点四:大力发展基于家庭服务的社会组织。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纽带,也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感情纽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将产生很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政府往往会由于公共服务能力的有限而无法回应,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则是最好的选择。对我国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这么多年,传统家庭互助体系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并潜存着巨大的社会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家庭在社会转型中的需求,并对这类的社会组织进行培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重点五:推动有意义的公众参与。“有意义的公众参与”有三个特质:其一,公众参与是否有明确的公共问题指向;其二,政府是否有可能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参与方式并以此减少社会排斥;其三,这些参与能否形成某种实质性的结果。“有意义的公众参与”其实反映的是政府与公众打交道的诚意与技巧。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欧洲国家流行的卓有成效的公众协商方法包括:居民顾问团、焦点团体、居民意见调查小组等等,并以此促成了良好的政—民互动效果。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公众参与无论在正式文件还是街谈巷议中都是常被提及的术语,但对大多数居民而言,我们对除了投票、听证会以外的其他参与技术依然非常陌生。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做法。
重点六:用社会逻辑来解决社会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社会领域的问题时经常重“堵”不重“疏”,重“处置”而不重“防范”,政治逻辑被直接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导致原本可控的问题往往以高昂的代价解决。当前我们要树立这样的观念:和谐社会也是存在冲突和分歧的,这些冲突和分歧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纾解并被社会所容忍。我们要有勇气并且学会用社会逻辑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在这方面,基层党组织建设大有作为。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稳定体系建设研究”首席专家、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