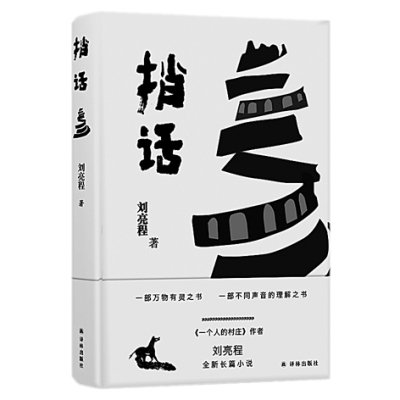
《捎话》译林出版社二○一八年十一月出版
《虚土》和《凿空》之后,作为小说家的刘亮程面临两种选择:是将《虚土》《凿空》里的散文痕迹祛除得更彻底,更接近时下小说家们一致认可和追求的“讲故事的人”,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路上行走,成为一个更具鲜明风格标识的小说家?《捎话》让我意外的是,他走了第三条路,即把自己变成一个在艺术上冒最大限度的风险、甘愿处于极端状态的小说家,营造一个将小说、散文、诗、戏剧、神话、民间传说等多种元素集中调动,汇聚成一个其他人不可能拥有的小说世界。
这是一部关于语言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声音的小说,说得书面一点,这是一部关于媒介与沟通的小说。但这一切都是呈现的结果,其时空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历史之外的虚构。它或来自某种神话,或本身就是作者创造的某种神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四处充斥着声音,人声、驴鸣、狗吠、鸡叫,它们各自以自己的能量在世界上存在着,没有人能看得见,却颇有秩序。在《捎话》里,声音是有形状、长度、颜色和速度的。语言是行走的,速度比人快。语言是武器,可以攻城拔寨,直接致命。小说以人物“库”和一只小母驴“谢”为主角,贯穿全篇,展开一个看不见却无比紧张的语言世界。
在《捎话》里,有两个势不两立的王国,即毗沙和黑勒,它们有着互不相通的语言。“库”是可以依靠语言天赋,依靠“翻译家”身份游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人物。而两个国家的驴,却并未因为人类的文明、语言的隔膜而无法沟通。两个互不相通的世界里,驴可以通过嘶鸣互相对话。“捎话”可以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职业,将一切对立和隔膜消除,实现有效沟通。当“库”牵着一头驴出发时,得到的指令是把驴“当成一句话”。语言是分裂世界的黏合剂,是在不可能被认知的状态下紧张地运行,它改变了世界,而人们却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捎话》拥有人、牲畜、亡灵三重世界。小说强调了这三重世界的互不相通,同时甚至更加强调了互相重叠、交叉与分裂的过程。驴成了一切皆通的媒介,它既可以知晓“库”的一切言语和举止,也能看见鬼魂的行踪,而“库”的能力是受限的,他就不懂驴的语言。
从艺术上讲,《捎话》具有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成熟要求。小说的故事线索、人物关联体现出作者长期的深思熟虑和巧妙构想,人、兽、灵三种行动主体各有小说意义上的分工,也有严格把控的独立与交叉,纷繁但有致,肆意而小心。小说性在其中是一种自觉要求。在保持小说性的同时,《捎话》追求小说故事的流动性,到处是别出心裁的高密度穿插。小说语言在保证故事推进力度和完整性的同时追求诗性风格。诗化语言特别表现在对人与兽所持“语言”的形容与比喻上。语言是有形状、长度、力度的。看不见的语言在作者那里却是可见的,甚至可以物化。人的语言千差万别,毗沙和黑勒的语言不一样,除此之外,人类还有许多种语言,不通是共同的特征,而“库”是唯一能听懂所有语言的翻译家,在人类语言的掌握上,他是全能的。而驴的语言是一样的。
将声音物化,在《捎话》里并不是比喻,而是一种形态的表达。究竟是谁有能力看到声音变成了可触碰的固态?是小母驴“谢”,有时候也是叙述者的直接表达。因此在小说里,不可见的叙述者最强大。驴鸣声多了,就变成“无数道彩虹架在夜空”,而且“万道驴鸣的彩虹拔地而起,跨过消失的城墙”。还有“风将声音拉成一只鞋形”。有形状的声音还有颜色。彩虹本身就是颜色,“红色驴鸣”在小说里出现多次,而人的声音是“土黄色的”。声音在动态中体现出长度,“世上的路都是驴叫声量出来的”。
小说中有很多妙喻,简直分不清是作者的发明还是从民间得来的,总之会心处甚多。如“驴见面不问年纪,问蹭倒几堵墙。”“在城墙上听驴叫犹如目睹繁星升空。”小说中还有一位人物说过:“我害怕一旦我学会了别的语言,就再也回不到家乡了,我会在别的语言里生活,乐不思归。”读来让人会心。我想起前不久陪作家王蒙回他的家乡河北南皮。回到家乡的王蒙一直用南皮话与亲友交流,乡友们感叹他对家乡的深情和语言天赋,王蒙则讲了家乡方言的意义。他说,家乡话让人有一种父母双亲还在的感觉。可见,语言和故乡的关系,跟一个人文化根基即所从何来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读《捎话》让我想起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在那部小说里,散文诗的笔法,让动物和植物说话,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不可替代的民族民间艺术,奇异的描写,令人感佩。就艺术追求和创作才华而言,《捎话》与之有相似处,在品质上也绝不逊色。不过,二者的区别在于,《我的名字叫红》是有具体地理方位的,伊斯坦布尔就是中心,也有明确的历史时段,在无穷的想象和诗意的描写中,国家、民族、历史的指向是明晰的。它既有溢出历史的章节,但总体上还在历史当中,同时小说还有当代故事框架,有着爱情、侦探等通俗小说要素,由此构建了一个多维空间。这部小说不极端也不绝对,可以在不同层面的读者中流传。
可以说,当代小说,无论中外,特别是在中国,正处在传统小说观念和现代小说叙事共存的时期。有时候它们在打架,有时候它们在互补。但相融带给小说更多的意味和复杂性,更能吸引不同层面的读者共同关注。
《捎话》的笔法,是刘亮程的原创。他是诗人、散文家出身,有着在多民族地区聚居的经验,受民间文化艺术浸润日久,对自然有着天然的敏感。当下的不少小说家纷纷转向“讲故事”,满足于浅表的故事和简单的主题,放弃应有的美学抱负和艺术理想,以为写了现实中的故事就是现实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当代小说亟待出现在艺术上有独特追求的小说家。刘亮程的努力令人感佩,《捎话》比《虚土》和《凿空》走得更远。《捎话》里的荒漠、戈壁、胡杨林等意象,或许可以让人想到与作者生活相关联的地域场景,即与“西域”有着“隐约”关联。但这些在小说里没有突出的标识作用。在保证作者奇崛大胆的想象和诗意、夸张、超现实的描写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下,我个人倒是觉得,也许这样的小说还可以多一些与现实人生世界相关的内容或元素。这既是一种叙述上的策略,可以扩大读者面,也考验着作者超验的能力,即如何更直接、更大量地与现实对接,并碰撞出奇异的火花。那或许会使小说更具意味,也符合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西方当代小说,特别是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并不那么深不可测。中国作家的创造力绝对不输给他们。
流行小说的外壳和包装,严肃历史的介入,烟火生活的穿插,民族民间文化的独特标识,诗意化的笔法,强大的叙事能力,深邃的人生与哲学思考,这些要素在一部小说里同时出现、相互交织,或许更考验创作者的综合实力。如果处理巧妙和足够称奇,就更能吸引读者的眼光,提高小说的传播力。
《捎话》里有明显的神话逻辑,也有现代小说的寓言品格,同时也有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觉要求。小说在看似浪漫、诗性、荒诞的描写中,有着严整的系统设定,而且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一种创作上的知行合一。无论对刘亮程个人还是对当前的中国小说创作,《捎话》都是一次值得认真对待、深刻剖析的突破与收获。
(作者:阎晶明,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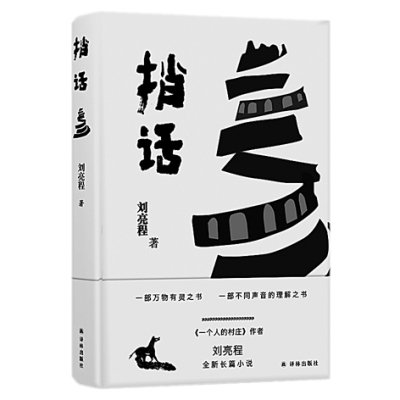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