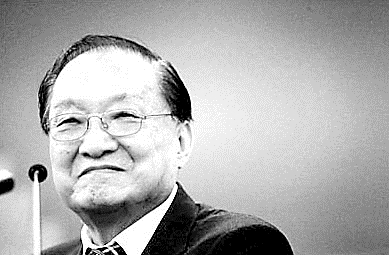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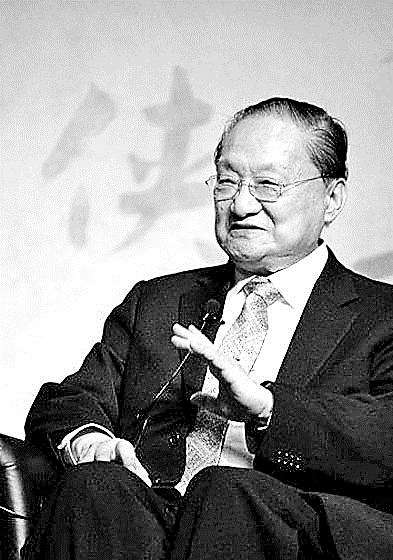

要论华人世界第一影响力的作家,说谁都会有争议,除了金庸。但要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普世性,估计有不少人会反对。比如就有人拿出王朔当年批金庸是港台四大俗说事儿。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市井文化的余韵,是通俗文化的结晶,是香港高度商业的快餐文化与中西交汇文明的产物。它的俗是畅销的缘由,也是经典的诱因。我们对通俗文化一直抱有一种很深的偏见,这种偏见是精英化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无知造成的。我们一度认为小说要么扎根于现实主义,要么青睐现代主义,就算你要写怪力乱神,也摆脱不了魔幻现实主义等正统文学史的思维。通俗文学只能作为消遣,无法承担文以载道的重任,进入不了文学史的大讲堂。但王朔批金庸四大俗最吊诡之处在于,王朔的小说被称为痞子文学,本身就是老北京通俗文化京味文化的留存,他反而看不上金庸小说的俗,也是咄咄怪事。
现如今大众文化勃兴,我们对金庸小说的认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重要的一点,当年少年时候读金庸文学启蒙的两三代人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他们对金庸的推崇,也把武侠小说这个当年不登大雅之堂的门类,扶上了文学的神龛殿。众多学界中人拥有话语权,撰写文学史,都把金庸列入了鲁郭茅巴之后的大师级作家。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才从一种文学史去魅的光环中正视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准。或者,我们干脆这样追问,金庸的武侠小说能不能称为华语文学的经典?
经典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仔细分析文学史上经典的形成,基本脱离不了几个标准,比如大众喜闻乐见的基础,专业批评家的推崇,时间的发酵——前两个还好把握,时间的发酵如何理解?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代人一直能够从中发现符合现时代的审美诉求,能够从中找寻到与现时代对话的基础。就如同莎士比亚从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乡村歌手,变成了普世永恒的艺术家,就是因为经过无数人无数次赞誉和时间的考验,把他变成了一个可以无限进行解读诠释的作家。
从影响力的层面上讲,金庸其实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当然,金庸与莎士比亚最大的不同在于,金庸花费了大半生时间亲手来打磨和塑造自己的武侠小说,想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送上经典文学的众神殿。说白了他其实也是个俗人。这倒不是就批评意义而言的,因为他是个精明的俗人,他才如此在意自己的武侠小说。他一生只写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越女剑》,长篇十二部,短篇三部,共计十五部作品。这些武侠小说都是在《明报》连载,这是通俗文学最常用的一种形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连载于1955年,最后的《越女剑》连载于1970年。此后,他声明封笔,众皆哗然,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说,那正是他创作生命力的旺盛期,他甘心封笔,自然做好了打算。这个打算就是,他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来修订自己的作品。大多数武侠小说家都不会像金庸这样敝帚自珍,如此看重自己的作品,比如古龙的小说,最后留下的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大概就是缺乏金庸的这种精细和远见。
我们可以说,金庸的后半生,投入到修订和宣传自己作品的精力已经远超一个作家的作为。别忘了,金庸是个报人和作家的同时,还是一个商人,他对自己武侠小说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在商业和电影电视改编上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比如江湖中流传着,当央视的张纪中要翻拍《笑傲江湖》的时候,他用一元的价格售卖自己的小说版权,这就是金庸的厉害之处;另外一方面,他广泛结交海内外华语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各位学者名人,比如当年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北大的严家炎教授撰写文学史的时候,就把金庸列入了当代文学史的大家之列。
金庸之所以如此严格地修订自己的武侠小说,无外乎就是想让自己的“武侠小说”把前面的“武侠”去掉,变成小说和文学。所以他念念不忘其他人对他的“吹捧”,在修订版的《天龙八部》后记中,他干脆说把此书献给在海外任教的著名比较文学批评家陈世骧教授,还特意指出,“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为什么说金庸是个俗人呢?别人私底下夸他,他一个人笑纳了还不够,非要在文章里写出来,写出来还不够,还非要在最后再把陈世骧写给他的两封信贴出来,让读者看看。这种可能不是虚荣心,而是对自己的武侠小说不太有信心的缘故。
关于金庸的俗。李敖爆过料,说的是有一年,金庸到台湾,跟李敖聊天,特别提到,在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说:“佛经里讲‘七注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窘得无以对答。李敖认为,金庸的信佛,是一种“选择法”:凡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现在回想起来,李敖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或者说,这种伪善正是大多数的选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解释,正因为这种伪善,这种俗世中人,才能写出如此好看的作品。金庸的俗是他的武侠小说好看的原因,因为俗是人情世故,是柴米油盐,是爱情的得与失,是人性的复杂与隐微。
少年时读金庸,读的是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江湖险恶,旖旎风流。中年时再读金庸,读出来百般况味,有政治,有人心,有权力,有自由,有无奈,有人生聚了又散,散了再聚的无常,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坚守与欢喜,有得不到的遗憾等等。武侠只是一个影子,文学才是金庸小说的最大底色。
金庸的一生对他的小说最大的执念大概就在于此,那就是他的武侠小说能不能成为文学,能不能与纯文学一较长短。我试着作出自己的回答,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但是文学,而且是华语文学界最好的文学之一。
对现在的华语文学而言,没有所谓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这种区分已经没有意义,文学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好文学与坏文学,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和风格,这些都不影响最终的评价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但是好的文学作品,还是影响力深远的经典文学。这就是我说他的文学具有普世性的原因,因为好的文学会向所有人和所有的时代敞开,让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接纳它成为自己的文学。我们每个人通过阅读金庸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物。我可以喜欢杨过,你可以喜欢令狐冲,更多人喜欢郭靖和萧峰,有人喜欢包不同,有人喜欢南海鳄神,有人喜欢桃谷六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种喜爱正是金庸小说成为经典的原因。因为一部成功的作品,不会只用主角吸引你,而是不荒废掉任何一个小人物。
自媒体时代,很多人通过解读金庸小说为业,这种解读充分证明了一部好作品的生命力多么顽强。它之所以在任何时代都能找到生存发芽的土壤,很简单的道理,“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艺术是创造,音乐创造美的声音,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小说是创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那么有了录音机、照相机,何必再要音乐、绘画?有了报纸、历史书、纪录电视片、社会调查统计、医生的病历记录、警察局的人事档案,何必再要小说?”
多浅显透明的道理,胜过正统文学家的千言万语,文学之所以是普世的,因为人和人性从未改变过。无论历史如何变迁,社会如何更新换代,文明如何发展,只要人依然是那个无毛两足会说话会思考的动物,我们就会时刻想念郭靖的拙朴,杨过的偏激,张无忌的犹疑,令狐冲的逍遥,萧峰的豪迈,韦小宝的狡诈,岳不群的阴险,左冷禅的阴鸷等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通过无数次翻拍的电视剧和我们阅读记忆中的人物形象不断地重叠在一起,每天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一个标杆和警醒。
这不正是经典文学的影响力吗?(思郁)
 提起小剧场话剧,傅维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绝对信号》到《恋爱的犀牛》,从人艺小剧场到国话先锋剧场,从大学生戏剧节到北京青戏节,从李六乙到孟京辉、田沁鑫……小剧场诞生三十多年来,每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一个标志性人物都与这个名字紧紧地“绑”在一起。
提起小剧场话剧,傅维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绝对信号》到《恋爱的犀牛》,从人艺小剧场到国话先锋剧场,从大学生戏剧节到北京青戏节,从李六乙到孟京辉、田沁鑫……小剧场诞生三十多年来,每一个标志性事件、每一个标志性人物都与这个名字紧紧地“绑”在一起。 张艺兴第二版本打歌现场持续高能燃爆,舞台美感完胜MV。“堪比跨年演唱会的打歌阵容,媲美演唱会的舞美制作”,随着观众与行业内对于节目口碑的持续发酵,后期陆续会迎来王源、邓紫棋、田馥甄、NINE PERCENT等音乐人的打歌舞台。
张艺兴第二版本打歌现场持续高能燃爆,舞台美感完胜MV。“堪比跨年演唱会的打歌阵容,媲美演唱会的舞美制作”,随着观众与行业内对于节目口碑的持续发酵,后期陆续会迎来王源、邓紫棋、田馥甄、NINE PERCENT等音乐人的打歌舞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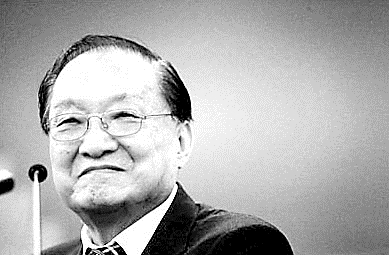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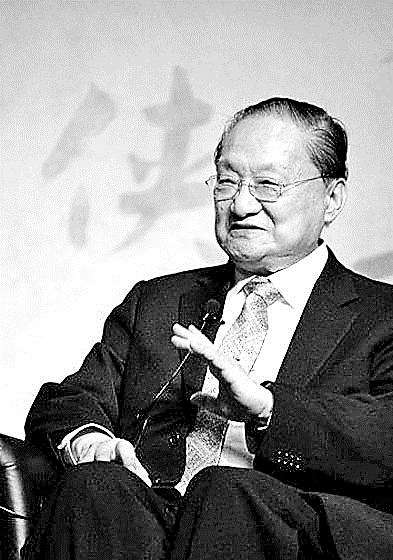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