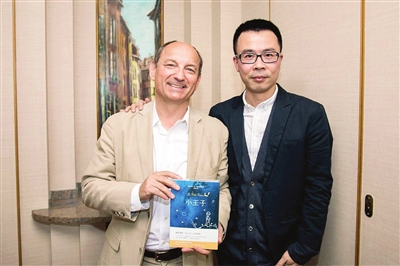
李继宏(右)在《小王子》作者的故乡

李继宏 生于1980年,翻译家,广东揭阳人,译有“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丛书,包括《小王子》《瓦尔登湖》《月亮和六便士》《喧哗与骚动》等,以及《追风筝的人》《穷查理宝典》等图书,译著总销量超过两千万册。
印 象
“80后”翻译家
译著销量两千万册
译者,是阅读世界中巴别塔的建造者,有了他们,思想得以跨越语言的障碍,从异域他乡跨越山河而来,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
国内历来的翻译大家,声名都不输于作者,林纾、郑振铎、冰心、傅雷、朱生豪、草婴……许多经典译著,都出自他们的译笔。而作为一个“80后”,李继宏受到的关注与评价,在这个年龄段的译者中是非常少见的。
从畅销的当代作品到早期的文学经典,李继宏的译著列表是很让人吃惊的。且销量也给出了市场对他的认可,《追风筝的人》长年热销自不必说,根据相关出版方提供的数据,《小王子》在今年6月已销出超过300万册,加上其他作品,总销量超过两千万册。
近日,记者从“果麦文化”获悉,李继宏推出了最新译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已经是“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的第八部作品。为了译好这部经典,李继宏用了两年时间,查阅了海量资料,到福克纳的家乡实地考察,甚至师从美国福克纳研究专家理查德·戈登进行学习。译本中的一些细节可见李继宏所下的功夫:仅注释就多达354处,且在小说译完后,他特意撰写了长达15000字的导读,全面介绍福克纳的生平、其与现代主义文学的渊源,以及《喧哗与骚动》的重要意义。这样雕琢一部译作,在快速阅读的氛围里并不多见。
李继宏并不是学语言出身,他大学时读的是社会学专业,毕业后在媒体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英语不错,机缘巧合在2003年获得了前往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颁奖礼的机会,从那时开始真正走进了外国文学领域。2004年夏天,有个朋友在MSN上问他,一家出版公司买了一本很难译的英文书版权,是否愿意帮忙翻译。李继宏当时工作正好不忙,便答应了,于是就有了他的译著处女作《维纳斯的诞生》。后来该出版公司买下《追风筝的人》翻译版权后,便与李继宏联系,催生了这本多年来始终畅销的译作。
2015年,李继宏赴《小王子》作者的故乡法国里昂,与“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创办人举行了认证签约仪式,他所译的《小王子》得到了基金会的支持和推荐。由于该基金会是《小王子》作者的侄孙创办的,这意味着李继宏的译本得到了作者家族的官方认可。
和流行一时的图书相比
经典更能带给读者启迪
记者:李银河将您的翻译称为“研究式翻译”,但这似乎和当下快节奏的出版以及阅读状态太矛盾了,感觉是一个稀缺型的东西,对此您怎么看?
李继宏:李银河老师一直很喜欢我的译作,她给《月亮和六便士》写过书评,前年拨冗参加了《傲慢与偏见》在北京的活动,今年又向读者推荐《喧哗与骚动》。她这种提携后辈的胸怀和好意,我是很感激的。
现在国内多数出版机构出新书的节奏很快,市面上流行的也大多是快餐式读物,不过这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欧美也是如此。但我始终坚持认真打磨每一部译作,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我相信和那些流行一时的图书相比,经典作品更能给读者启迪,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工作引导更多读者来看这些人类文明的精华。第二,图书市场非常特殊,是一个真正优胜劣汰的市场,长远看不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有些快餐式读物也许短期能卖很多,但需要在营销上花很大力气,并且热度往往只有几个月,而经典作品的销售是持续的、稳定的,像“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虽然几乎没有做宣传,但自从2013年1月问世到现在,前七种累计销量已经超过500万册。
记者:您非常喜欢给译文加注释,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有没有担心过,注释太多会让阅读变得有点“碎”?
李继宏:语言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它不是简单的字母或者笔画的组合。比如说我们汉语里面讲“黄粱一梦”“逼上梁山”或者“明日黄花”,这些都含有比字面丰富得多的意义,你要把它翻译成外语,不加变通或者注释的话,目的语读者肯定是看不懂的。英语也有很多类似情况,比如《喧哗与骚动》里一些引用《圣经》的段落,或者美国南方特有的一些物件,如果不加注释,普通读者很难明白什么意思,会影响他们领略作者的用意。
“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有很多注释,我的用意是帮读者全面地、彻底地去理解这些杰出的外国文学作品。至于你说的注释太多影响阅读的问题,一方面我拒绝脚注,所有注释都是尾注,就是为了尽可能保留正文的连贯性;一方面经典作品和通俗作品不同,它们需要反复阅读,而不是读一遍就扔开,这时候注释便显得尤为重要。
记者:撰写长篇导读也是您的一个特点,写这样的文章是不是比翻译更耗神?
李继宏:我写导读和加注释的用意一样,也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西方小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早已变得非常专业。你要是去看英国或美国大学英文系的网站,会发现那些教员的研究方向分得特别细,有的研究维多利亚文学,有的研究莎士比亚,有的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文学。经典作品需要很深入的研究才能读懂,比如《傲慢与偏见》,为了真正理解这本小说,我们需要知道18世纪英国的法律风俗、饮食习惯、服饰风尚等等,所以在翻译这本书时,我查阅了数以千计的文献,为我的译本添加了几百处注释。但注释只是讲解细节,我认为还需要一篇导读来为读者提供一个整体上的理解方向。就好像普通观众去博物馆看展览,看到一些出土文物,需要专业的解说才能明白。我通常是译完书、加好注释后再写导读,写起来的确耗费心神,但相当于收尾。对我来说,只有写完导读,整本书的翻译才算正式结束。
原著和译著是不同作品
文学翻译不必逐字逐句
记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怎样克制自己的出现?
李继宏:早些年欧美的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隐身,认为好译者必须是透明的,要隐藏在作品后面,不能显露个人痕迹。你去看英国或美国出的翻译作品,封面很少出现译者姓名。但这种理论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原著是原著,译著是译著,它们分属不同语言,生产者也不一样。这种理论已经过时,现在欧洲学术界认识到原著和译著是不同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功能,所以开始强调译者的显身,把译者放到一个核心的位置来研究。今年5月维也纳大学便召开了一个叫作“为文学译者搭舞台”的国际研讨会。
莫言的英文译者葛浩文曾经说过,英语读者看他的译本,读的不是莫言,而是葛浩文。我赞同他的看法,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从没想过要克制自己出现,实际上就算我想克制也做不到,因为无论怎样,书总是我译的,毕竟每个字、每个标点都是我亲手打出来的,不带个人色彩怎么可能呢?
记者:作为翻译家,您怎么理解翻译中的“忠实原著”?
李继宏:“忠实”或说“信实”,是人们在衡量翻译时经常提到的标准。翻译当然要讲“忠实”。在翻译商品使用说明书、法律文件等较为简单的文本时,忠实的标准容易确定,用它来衡量翻译质量是合适和方便的。但对文学作品来说,这个标准很难确定,因为文学作品非常复杂。就拿语义来说,哪怕是简单的词汇,也有很难判断的时候。比如说take这个单词,很简单对吧?但在《牛津英语词典》里,它有85个义项,有的义项下面还细分八九个小项,译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一个妥当的译法。这时候译得是否“忠实”,恐怕需要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士才能判断。另外,涉及言外之意、写作风格之类,就更复杂了。
总的来说,文学翻译的“忠实”很难定义,但绝对不是逐字逐句翻译。国内很多读者甚至研究者,对文学翻译的“忠实”的理解还停留在拿一本双语词典找差异的层次上。欧美读者很少有这种观念,像莫言的作品,英译者改写非常多。
译著销量达两千万册
仍是默默无闻穷书生
记者:很多人批评现在的环境、条件很难催生好的译者,比如对译著的学术业绩认可度低、翻译费太低,您觉得这些是关键因素吗?
李继宏:你说的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这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根源在于文学翻译的职业化程度不够。一方面专职文学翻译很少,大多数译者要么在大学教书,要么在出版社当编辑,甚至是在校学生,如果一个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兼职人员构成,薪酬水平是很难提得上去的,因为从业者对这份收入的敏感度很低,争取提高报酬的欲望也不会高,兼职者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在正职上,翻译出来的东西自然很粗糙。另一方面是缺乏客观的业内评价体系,你说对译著的学术业绩认可度低,这说明文学翻译没有得到行业外的认可,但目前中国文学翻译更糟糕的情况是,它连业内的评价体系也没有。我举个例子,比如职业篮球,我们知道姚明的水平很高,他的职业收入和在球场上的表现远远超过国内其他球员,所以普通观众不会质疑姚明的专业水准。但文学翻译的情况不同,许多杰出的译者,比如林少华老师,常常被一些读者,甚至同行嘲讽。那些人嘲讽林老师的出发点其实很可笑,常常是因为不喜欢他的文风,有时是因为林老师译文中犯了小错。这就像篮球观众因为勒布朗·詹姆斯在比赛时偶尔走步就嘲讽他不会打篮球一样可笑。如果不建立客观的业内评价体系,文学译者恐怕很难得到适当的业外认可。
记者:很少有译者能在您这个年龄有这样的收获,您觉得您的翻译之路有可以复制的地方吗?
李继宏:这很难说,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我从24岁开始翻译书,到现在15年过去了,假如说有什么关键因素促使我走到今天,我想大概是热爱和专注。做文学翻译光有兴趣是不够的,因为很难做得好,做的过程会遭遇许多困难和挫折,哪怕做得很好,也不能带来名利──你看我译的书卖了两千万册,依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如果不是对这件事特别热爱,恐怕难以持之以恒,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只译了几本书。专注也很重要,像我几乎没有娱乐和社交活动,过去十几年,除了有时和我太太出去旅游或考察,平时大部分时间在书房里,不是对着书就是对着电脑屏幕。不过好像无论从事任何行业,想做好都需要这两点。(文 张玥)
李继宏有话说 译者要保持原著的情感力量
我父母只念过几年书,但他们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学。我父亲会写古体诗,会制灯谜,主持过几年元宵灯谜会。而我现在关于童年最早的记忆,则是母亲指着墙上挂的唐寅《落花诗》,从“刹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开始,一直背到“颜色自来皆梦幻,一番添得镜中愁”。
我小时候生活在粤东乡下,当时不要说英语,就连普通话也很少有人说──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上课用的是潮汕话。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我直到19岁上大学才开始说普通话。在这种强方言环境里面,人们很难对外语产生兴趣,我也不例外。
我从初一开始学英语,第一次英语测试,考试内容是默写26个字母和几个单词,班上好像二十几个同学考了满分,我才考了六十几分,当然后来成绩慢慢上去了。1995年暑假,我在潮州一家书店买了一本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国内译成《廊桥遗梦》),其实也看不懂,但就是很喜欢,开始主动学习英语课本以外的内容。因为我们镇没有高中,暑假后到隔壁镇另一家学校,那里的图书馆订阅了一份叫作21st Century的报纸,高中三年我几乎一期不落地看完了。
第一次做译者,说实话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如果曾有过,那么也已经忘了。当时没有经验,译得很快,《维纳斯的诞生》20万字左右,我大概花了一个月便交稿了。这本书在2016年出了新版,我修订了挺多处理欠妥的地方。
后来翻译《追风筝的人》,第一感觉是故事很吸引人,文笔也挺简单。翻译过程中,我特别留意的是如何保留原文高度的易读性、紧凑的叙事节奏和充沛的情感力量。从这本书的畅销程度来看,我的目标大概是达到了。
《小王子》是我自己要翻译的,不是出版方派给我的任务,所以可能算不上挑战。我译这本书的初衷,和译“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其他书是一样的,就是想让读者真正读懂这些经典。比如在我的译本出版之前,《小王子》一直被当成儿童文学,我在译本导读中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就是一本存在主义杰作。现在我的解释已被广泛接受,包括作者的后裔、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主席奥利维尔·达盖先生,也十分赞同我的看法。
在所有我翻译过的作品中,最难的就是《喧哗与骚动》。我没看过其他人译的福克纳──自从“李继宏世界名著新译”上市以后,常有人问我对以前的译本怎么看。这么问的假设是,我翻译这些书时会参考以前的译本,但实际并没有。文学翻译和弹琴、做木工、烹饪一样,本质上是门匠艺,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匠人在工作时去询问其他经验不如自己丰富的同行。另外来说,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翻译一本书通常要看海量的文献,除了作者的全集和传记,还有关于其作品的研究论文及专著,等等。比如我翻译《喧哗与骚动》,大概有四分之一时间是用在研究美国南方的历史,如果不去研究这些,《喧哗与骚动》里面有大量段落是难以理解的。
 昨(14日)日,演员黄轩团队跟随电影频道“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的西藏扶贫之行来到了最后一站——拉萨,他先后参观了拉萨市的农业产业园的蔬菜交易厅和奶牛养殖中心,这些独具特色的拉萨产业园带来了好的产值同时也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昨(14日)日,演员黄轩团队跟随电影频道“脱贫攻坚战——星光行动“的西藏扶贫之行来到了最后一站——拉萨,他先后参观了拉萨市的农业产业园的蔬菜交易厅和奶牛养殖中心,这些独具特色的拉萨产业园带来了好的产值同时也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构筑了一个中国武侠世界的金庸先生驾鹤仙去,时隔几日,打造了美国传奇漫威世界的漫画元老斯坦·李也离去了。美国当地时间11月12日,“漫威之父”斯坦·李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
构筑了一个中国武侠世界的金庸先生驾鹤仙去,时隔几日,打造了美国传奇漫威世界的漫画元老斯坦·李也离去了。美国当地时间11月12日,“漫威之父”斯坦·李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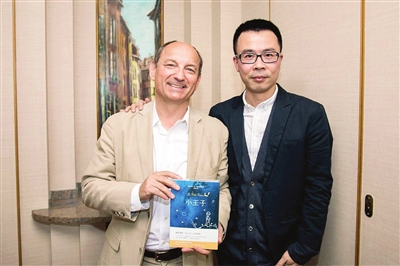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