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还真都是车站有事。”杨存信回忆着说,“老爷子太清楚了。”
杨家父子在青龙桥火车站守了67年,两代人,大半个世纪。对铁路人来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青龙桥车站的工作人员每天早上8点半开例会,随后要进行的是常规的考核,包括选择题和情景模拟题。
杨存信很庆幸,这么多年,车站和自己一直都平平安安。再过4年他就要退休了,那时新的京张高铁已经建成,新线路全长174公里。杨存信开玩笑:“正好不耽误我看冬奥会。”
詹天佑砸入了第一颗道钉
100多年前,詹天佑用“车头换向”的方式,借山势巧妙规避了八达岭山脉的险峻,让火车扭成一个人字形夹角翻过了陡坡。百年后,正在修建的八达岭隧道将在崇山峻岭中,直接打出一条通路来。
新八达岭隧道全长12.01公里,下穿水关长城和八达岭长城。1号斜井位于水关长城附近,与八达岭长城旁的2号斜井同时开工,最终将在山体中汇合贯通。
这条隧道采用的挖掘方式并非时下流行的“盾构机”,而是相对传统的钻爆法,爆破时产生的振速和分贝都被降到最低。挖掘工作深入山体,这种工程被称为“暗挖”。两根直径1.5米的通风管道从井外伸进洞里,鼓风机每时每刻都在发出巨大的“呼呼”声,人们说话时,要把嘴凑在对方耳边喊。
杨金显是京张高铁八达岭隧道1号斜井队的队长,今年31岁。2007年,他成为中铁五局的一员。十几年来他都工作在这样的隧道里,头上顶着头盔,白天看不到太阳,呼吸的空气里总是带着泥土的潮气。从隧道里出来时,大量的新鲜空气会在一瞬间涌入鼻腔。
八达岭地质情况特殊,围岩情况变化很大。在暗挖工程里,围岩专指隧道周围受到开挖影响后,出现应力改变的岩体。
“这是我接触隧道工程以来,遇见的最难的一次。”杨金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之前他参与的隧道工程大多围岩情况稳定,可以使用相对统一的挖掘方式。许多人都以为在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一带修建隧道会更难,但据杨金显解释,那些地方的地质结构更稳定一些。
相比之下,新八达岭隧道才是他啃过的最硬的骨头。
在逐渐插入山体的两个斜井当中,“每一炮炸开后,围岩的情况都跟之前不一样”,有时遇到的是整块的岩石,有时周围满是碎裂的断岩,有时甚至会遇到湿陷性黄土或变形的软岩。地下水也常常会从挖开的地方渗出。
在八达岭区域,地下水的深度随着季节变化,难以预测。杨金显说,每天从斜井里抽出去的涌水,能填满一个小游泳池。
项目部成立了科技攻关小组,用多层分组喷射混凝土等方式,组成围岩的主动支护结构,以保证隧道不会突然垮塌。
“我们使用了一种新的品字形开挖的工法。”中铁五局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技术负责人许琪对记者说,“这种工法是‘顶洞超前、分层下挖、核心预留、重点锁定’。”
他正站在2号斜井深处,挖开的拱形隧道已经用混凝土支撑得足够结实。他身前不远处,正待开挖的一处新“品”字刚挖通最上面的一个“口”。在他身后,橙色的“全液压可调式超大断面台车”几乎填满了整个隧道。这架新型的台车,也是为了满足新八达岭隧道与八达岭长城站之间的大跨过渡段的工程需求而专门设计的。
同样是由于八达岭山脉复杂的地质情况,113年前,詹天佑选择依着山势,修建人字形铁路。
彼时他44岁,自耶鲁大学留学归国后,在当时的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他参与了京津路、关内外铁路的修建,由他主持建造的滦河铁路大桥,至今矗立在滦河河滩上。
那时,张家口是北平与西北连通的必经之处,毛皮、茶叶、丝绸、布匹,驮在上万头牲口的背上,每日往来于居庸关到张家口方向的商道上。修建一条铁路,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是迫切需要的。
“惟查距八达岭南二里余,名青龙桥,向偏东北,名小张家口,中有黄土岭,较八达岭稍低,轨路行径该处,虽绕越多十余里,似可减开凿之工。”他在呈奏给清政府的《修造京张全略办法》中写道。
京张铁路关沟一段的坡度很大,若要绕开这里,线路成本和工期都要大大增加。那时的蒸汽火车牵引力不够,不能直着爬陡坡,詹天佑便让它斜着爬,创新设计了“人”字形铁路线路,降低爬坡度。火车到了南口,用前后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开到青龙桥车站,进入“人”字形岔道口,便换过两个车头牵引的方向来,斜斜地从另一个侧面下坡,上下坡便显得容易多了。
当时,英国和俄国同时在争取这个项目的修筑权,还嘲讽说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恐怕还未出世,但清政府最终决定,把这条铁路交给詹天佑。詹天佑给自己在美国的老师诺索朴夫人去了信,忧虑“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
1905年12月12日,詹天佑和工程师陈西林一起,在北京丰台柳村主持了开工典礼。在全线起点的第三根枕木右轨外侧,他砸入了第一颗道钉。
用摄影记录这1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4年,首都档案馆开展了名为“百年京张铁路轨迹”的调研,调研团队来到了青龙桥火车站。在对方带来的一本书里,几张民国老照片引起了杨存信的注意。
其中一张拍摄于1937年6月30日。照片里,穿着军装、背着大刀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士兵站在青龙桥车站站台上,一旁的站房里,半圆型拱顶门下站着当时的青龙桥站站长。照片的拍摄者,是民国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
这些照片杨存信先前从末见过,“填补了民国时期京张铁路、尤其是我们车站的一段历史空白”。他用手机翻拍了几张,发给了铁路摄影师王嵬。王嵬专门联系到孙明经的儿子,得到了一个故事。
那一年,民国政府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西北考察团,孙明经是其中一员,彼时京张铁路已经运营了28年,西行的火车经停青龙桥火车站,孙明经在这里拍下了数张照片。
当时的站长向孙先生讨这张照片,要留作纪念。孙明经答允了,考察团继续向西。还未等他践诺送照片回去,便遭逢了卢沟桥事变。
关于这张照片的承诺,就此耽搁了大半个世纪。孙明经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甚至嘱咐儿子,找机会把照片送过去。
2015年6月30日,孙明经年过七旬的儿子,和王嵬一起来到了青龙桥火车站,把照片送到了杨存信手里。这张照片如今被放大装裱,悬挂在车站贵宾室的墙上。
去年的6月30日,王嵬站在和当年同样的拍摄位置,拍了一张同样角度的新照片。他想“对比着看看青龙桥站的变迁”。两张照片光线相仿,八达岭山势如昔,长城沿着山脊蜿蜒而下。相较于80年前,岭上的树木似乎葱茏了许多,站房后的一株大柳树比原先高了些,站前的拱顶加装了门。诸如电线之类的新事物,也出现在了照片里。
前些年,张家口站拆除了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站房。王嵬知道了这件事,这个90后年轻人,决定“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京张铁路”。
王嵬沿着铁道线,从丰台柳村的始发点,迈着双脚一路走到了张家口车站。每路过车站、公里标、水塔、隧道等地标,他就举起手中的相机,按下快门。他遇到过许多曾在这条铁路上工作或生活的人,与他们聊天,从只言片语中,窥探那些流散在岁月中的故事。
“我不想炒历史的冷饭,只想记录下这条路上,这么些人,这10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王嵬说。
他遇见一位老站长,祖父跟着詹天佑一道从老家广东北上修铁路,就此在北平定居,祖孙三代都是铁路人。一位叫徐景春的老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那是王嵬采访过的、唯一一位曾驾驶过马莱4型蒸汽机车的人。
 6月4日,正在忙于军旅电视剧《反恐特战队之天狼》拍摄的魏晨已正式接到邀请,将献唱《亚洲雄风》歌曲复刻,为中国代表团加油鼓励。魏晨也坦言非常荣幸,无论是参与圣火的传递还是演绎这样一首气势磅礴又充满时代烙印的经典老歌,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第一次参加亚运火炬传递,真正的去体会运动无国界的真实沟通。据了解,歌曲目前已低调完成录音工作。阿菲
6月4日,正在忙于军旅电视剧《反恐特战队之天狼》拍摄的魏晨已正式接到邀请,将献唱《亚洲雄风》歌曲复刻,为中国代表团加油鼓励。魏晨也坦言非常荣幸,无论是参与圣火的传递还是演绎这样一首气势磅礴又充满时代烙印的经典老歌,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第一次参加亚运火炬传递,真正的去体会运动无国界的真实沟通。据了解,歌曲目前已低调完成录音工作。阿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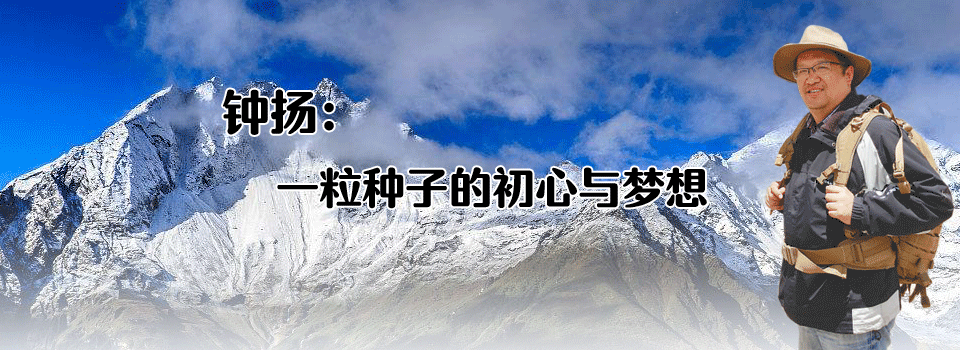










 ×
×